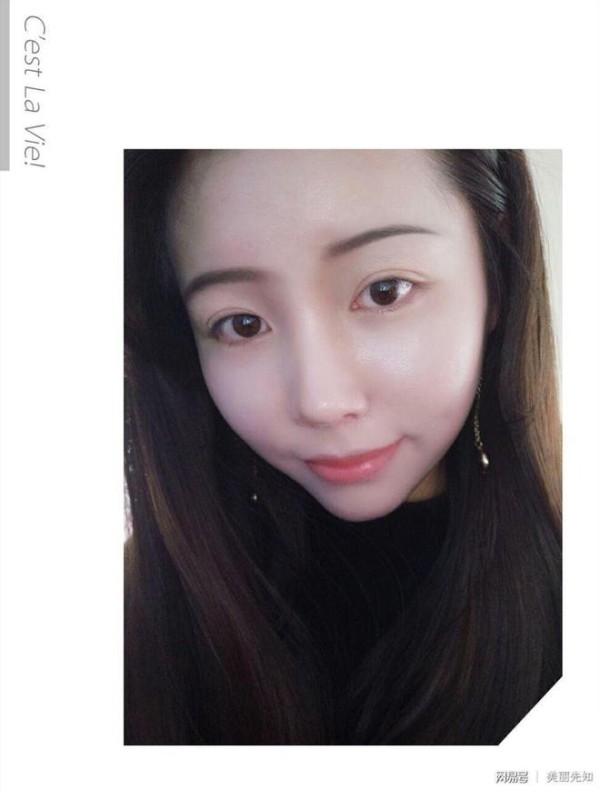中古史荐读|荣新江:悼念项楚先生——中国敦煌学的中坚

中古史中心|荐读
荣新江《悼念项楚先生——中国敦煌学的中坚》(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前言: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周一良是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2025年2月4日上午收到张涌泉兄的微信,告知项楚先生早上去世。印象里这些年项先生很少出来活动,但一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工作。不过涌泉说他这几年身体一直虚弱,最终不幸离世,享年85岁。项先生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5年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80年起任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以及该学会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代主任。
一
我最初听到项楚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我们老师辈的敦煌学圈子里。1983年10月,国内出版了一本《王梵志诗校辑》,根据28种敦煌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首次编成较为完整的王梵志诗集。其实这在收集、整理王梵志诗上是有功绩的,但王梵志诗流行于民间,抄本俗、别字满纸,又多为唐朝口语,校勘难度较大,理解也容易偏差。此书一出,就引起一些批评。像我们北大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具有小学功底,又有敦煌学素养,曾经参与《敦煌变文集》的编纂,看过这本王梵志诗的整理本后,就撰写了《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后来,北大的几位先生看到项楚发表的有关王梵志诗词语辨析的文章,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实力的学者。1985年夏天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时,季羡林、周一良等见到了项楚,知道他正在对王梵志诗做全面的校注,于是决定给与大力支持。关于此事,现在网上常常只说到季羡林先生,其实主要操办此事的是历史系的王永兴先生。我当时是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给几位敦煌学的先生们跑腿,记得王先生让我把王梵志诗的卷子从缩微胶卷冲洗成6×10cm大小的照片,陆续寄给项楚。后来项楚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及《续拾》,总共大概有五十万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三位先生通读了稿子,认为质量很高,所以决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上,打破常规,一口气发表出来。我那时已经毕业留校,主要工作就是帮几位先生编这本《论集》,为了出版方便,《论集》采用手抄的形式,免得那么多俗字、别字要造字,文书格式也很难排。负责抄定稿的老师住在西直门一带,我就成为从北大骑车到西直门往返传送稿子的人,也一遍遍帮先生们做校对工作。
终于在1987年6月,第4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所以这样赶工,是因为听说日本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教授要给这本《王梵志诗校辑》写书评,按照入矢过去批评《东京梦华录注》等书的做法,这篇书评一定会让中国学者非常难堪。与此同时,中国敦煌学圈子里盛传入矢的同事、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曾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加促使北大的几位先生要把一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当一篇论文发表出来。这一招儿果然奏效,入矢教授看了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后,写了一篇短评,盛赞其有水平。虽然当时我还无缘见到项楚先生的尊容,但在帮忙校对《王梵志诗校注》稿子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常常被项先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随手检出最符合的段落来对王梵志诗加注,感到极为敬佩。

一般人谈到北大先生们与项楚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其实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也是最后一辑)上,又一口气发表了项楚的三篇文章,即《〈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敦煌本〈鷰子赋〉札记》,出版于1990年5月。这三篇文章从53页到122页,篇幅也不算短,这说明北大的先生们不仅仅关心他的《王梵志诗校注》,还对他的敦煌讲经文、变文等其他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同样给与极大的支持。而项楚也把自己最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集中贡献给北大的论集,可以看出也是一种对北大先生们的学术回报。以后,北大的先生们继续在学术上大力支持项楚的研究,他也积极回应。比如他给李铮老师编的《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贡献了《〈五灯会元〉点校献疑续补一百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给王永兴先生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贡献了《敦煌写本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诗校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开始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时,第一卷他贡献了《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些北大方面的主动约稿和项楚的积极回应,更加推动了项楚有关王梵志诗等方面的研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学术佳话其实远比只有《王梵志诗校注》的发表更为丰富和圆满。
二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见到项楚先生了,他是一位内向的学者,不太主动说话,我们的交往更多的是以书信的形式,还有就是他出了书基本上都送给我,我也把新出的书呈上请教。我收到他的书之后,一般都会仔细拜读学习,颇有收获。这里就他的书出版后的相关故事以及我学习的体会,略示一二。
项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初版于1990年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是按《敦煌变文集》原编者关于“选注本”的设想而编的,共选入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佳的敦煌变文,也兼顾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的各类作品,计27篇,可谓集中了敦煌变文作品中的精华。录文以《敦煌变文集》为底本,《敦煌变文集》未收的《双恩记》则以《敦煌变文集新书》为底本,吸收自《敦煌变文集》以来许多学者及作者本人的校勘成果,汇成校注,附每篇之后。值得提到的是,这个选本里所收的变文,如《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舜子变》《伍子胥变文》,都是十五年前入矢义高编《佛教文学集》时选编的篇目,该书1975年2月由东京平凡社出版。入矢教授不仅关注王梵志诗,他也很早就写过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评(《中国文学报》第11号,1959年),也写过魏礼(Arthur Waley)编译《敦煌的民谣与故事选集》(BaI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an anthology,即《敦煌变文集》部分英译本)的书评(《中国文学报》第16号,1962年),在本书中则是从佛教文学的角度,选取上述变文加以日译,并附有注释,这是较早的变文注本。我不知道项先生在做自己的《敦煌变文选注》时是否参考过这本书,但项先生的书在文字校勘和注释详赡上都远胜一筹。另外,我还曾将其中的《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张议潮变文》,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著《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198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对读,深感项先生的学术功力之深。《敦煌变文选注》一书200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本,分上下两编,上编即初版内容,下编增收《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庐山远公话》等17篇,更是嘉惠学林。
项楚先生的《敦煌文学丛考》1991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他有关敦煌文学的论文24篇,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在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有些我已经读过,但这次汇编成集时又作了修订、增删和调整。翻检我的初版本《敦煌文学丛考》,许多地方都留有阅读的痕迹,有划线,有写在天头地脚的笔记,现在重读,还能够体会当时阅读中的愉悦。比如他考证《敦煌变文集》卷一《张议潮变文》后附录的P.3645歌颂“太保”的唱文,其中四句诗应当是套用自五代时江西吉水的隐士曾庶几的《放猿绝句》,并发议论:“以五代战乱频仍之际,一位南方布衣隐士的一首小诗,竟远涉山水,传至西陲,并被采入歌唱‘太保’的唱词中,可以证明敦煌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仍是十分密切的。”(17页)他的这个看法,对我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给予很大的启发。又如他考释《鷰子赋》中“括客”时,提到《佛祖统纪》卷三九引良渚提到的宋朝法令禁止的左道书籍,除摩尼教《二宗经》外,还有《开元括地变文》(77页);他指出《李陵变文》“仍差有旨拨者”的“旨拨”应订正为“叱拨”,为西域良马名,并举李石《续博物志》和唐诗例证(95页)。如此等等,对我都是深有教益的文字,不仅仅在敦煌学的范围,还包括唐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当然,他有关王梵志诗并非出自一人,而是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梵志体”诗歌合集的看法,我也觉得是真知灼见。
他的《王梵志诗校注》1991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上发表的文稿的整理本。到201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订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全书共搜集王梵志诗390首,厘为七卷,加以校注,成为最完备和权威的王梵志诗全集。我在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校样时没有时间琢磨,接到第一版《王梵志诗校注》后,仔细过了一遍,真的是受益良多。关于此书应当特别提到的是,2015年1月东京笠间书院出版了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辰巳正明的《王梵志诗集注释:读敦煌出土的佛教诗》(王梵志詩集注釈:敦煌出土の仏教詩を読む)一书,就是以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为底本,有王梵志诗的录文、训读、简注和现代日语的翻译,诗歌的编号就是按照项楚原著,注释也多所依从。讲项先生在王梵志诗研究上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故事,不应当忘记这个后续的出版物。
项先生《敦煌诗歌导论》的篇幅不长,原本是应台湾林聪明教授之约,给《敦煌学导论丛刊》写的专著,列为第9种,1993年5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6月成都巴蜀书社再版。书计五章,分别讨论文人诗歌、释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和王梵志诗,包括诗歌的性质、撰写时间、作者或研究情况等,可见项先生在敦煌文学方面更广博的知识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也仔细拜读过这本著作,并作为自己研究的依据。比如P.3720、P.3886、S.4654悟真大中五年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我引用时即参考了项先生的录文;又如我在讨论P.3445《赞法门寺真身五十韵》时,也参考了他的录文,并提示他对此诗性质的判断:“此诗忠实地记录了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迎谒法门寺佛骨时举国若狂的场面。”可以说,项先生不仅仅对王梵志诗有研究,而且对所有敦煌的诗歌,甚至唐人诗歌,都有通盘把握,甚至有自己的考证,如上述曾庶几的《放猿绝句》,就订正了《全唐诗》的错误。

项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是对任中敏《敦煌歌辞总编》的订正,有文字辨正,也有文义剖析。本书1995年1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列为林聪明主编的《敦煌丛刊二集》第3种。2000年6月巴蜀书社出版了修订本,对一些俗字又有校改与补充。此书大陆版项先生照例寄给我一本,我还能在电脑中找到2000年12月7日给他的回信:“承蒙寄赠新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不胜感激。大著不仅有订正台湾版误排之处的必要,也有出版大陆版的必要,因为台湾出版的书,不是大多数大陆学子可以看到的。前不久审读(某书)稿,歌辞仅用任书而未及大著,其中未能校出的字词极多,可见大著出版的及时。承您关照,张勇、刘长东也寄来他们的大著。您主编的这套《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内容扎实,对古典文献学的许多方面都有所贡献。”信中已经把我学习的一点心得,汇报给项先生。
他给我每一本书,我都有回信,纸质的一时难以检出,电脑中比较容易找到的还有一封,是2000年6月29日收到《寒山诗注》时写的:“久疏问候,念诸事顺遂。顷从朱庆之学兄处收到您惠赠的大著《寒山诗注》,不胜感激。这是《王梵志诗校注》之后您的又一部大著,有校,特别是有详细的注释,对于学殖不深如小生者帮助尤多。先此致谢,日后一定好好拜读。”《寒山诗注》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有意思的是,入矢义高教授也治寒山诗,但我还没有对过两家的工作。
项先生的学术论著,到2019年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项楚学术文集》中,包括《寒山诗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等五种学术专著,以及《敦煌文学丛考》《柱马屋存稿》《柱马屋存稿二编》三种学术论文集。

三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项楚先生做学问,喜欢单打独斗,很少与人合写文章,但也有例外。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为推动敦煌学研究和带动香港的学术研究,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陆续邀请大陆的敦煌学者赴港做学术研究,首批聘请的人物就是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和四川大学的项楚教授,我也在随后的1992年冬至翌年春,受邀到香港从事敦煌文献整理工作。此前饶公请项楚教授据缩微胶卷把他感兴趣的敦煌本邈真赞统统录了一遍,因为我在做归义军史研究过程中,在1985年和1991年两度游学英、法两国,曾经据原卷校录了大多数敦煌本邈真赞。于是饶公让我把项楚先生的录文和我的录文合在一起,计92人的邈真赞,每篇录文后有校记,形成《敦煌邈真赞校录》稿本,前面加上姜伯勤教授的《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和我的《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两篇长文,附录我写的《敦煌邈真赞年代考》,还有写本编号索引及参考文献,合编成《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一书,题饶宗颐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1994年7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列为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三。我后来考虑到两篇长文都已经分别收入个人论集,但邈真赞的校录则一直没有再版,所以曾经两次和项先生提起是否合作重新整理一下,在大陆出版一个增订本。他表示赞同,但他没有动手,我也没敢造次,所以这本邈真赞的“增订本”一直也没有出来。现在项先生遽归道山,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本应当抓紧时间,早点合作完成才是。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周一良是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编辑|陈子衿
网址:中古史荐读|荣新江:悼念项楚先生——中国敦煌学的中坚 http://c.mxgxt.com/news/view/736846
相关内容
著名敦煌学家、语言学家项楚逝世,享年85岁四川大学教授项楚数十年钻研校勘考据——在古典文献中潜心求索(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建筑史研究与敦煌石窟——从新史料看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
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共赴“冰丝带上的敦煌梦”
“满世界寻找敦煌”专题展在莫高窟开幕
敦煌艺术里的中秋节
文化中国行 | 专访常沙娜:花开敦煌 一生所望
《敦煌遇见卢浮宫》作者罗依尔: 我用“艺术脱口秀”讲敦煌|读+
浸润式阅读,让读者爱上大美敦煌
韩天雍:怀念我的导师刘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