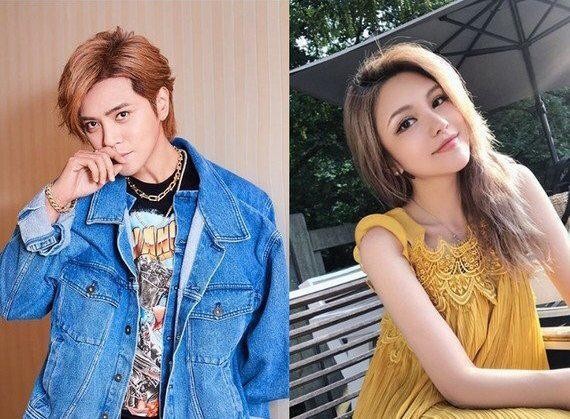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
——认识论中的“法国风格”
让-弗朗索瓦·布劳斯泰因 文,東亜 译,
本文译自:Jean-François Braunstein, "Bachelard, Canguilhem, Foucault. Le «style français» en épistémologie",in Les philosophes et la science, (Paris: Gallimard, 2002), pp.920-60.
感谢译者授权
似乎在哲学之中,谈论一种 “民族风格”是矛盾的,而在科学哲学之中则更是如此。毕竟,国境与对普遍性的追求并不相容。但是,在当代法国科学哲学中,似乎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
外国观察者们对这种“家族氛围”(air de famille)印象深刻。当加里·古廷(Garry Gutting)向英美读者介绍欧陆的科学哲学时,他提及一种“法国网络”(French network)。这一“网络”包含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当皮特罗·雷东迪(Pietro Redondi)为印度读者编选法国科学史家的文集时,他提到了科学史中的 “法国之争”(débat français)。这一时期最好的两位专家一致承认,在科学哲学中存在着某种法国传统。
这种共同特征同样也被一些其他的观察者所注意到。这些观察者虽然是法国人,却外在于,甚至敌视这一潮流。例如,万森·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同意,确实存在一个“法国实证主义学派,这一学派被认为是在研究不同知识专业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概念的历史”——而福柯正是诞生自这一学派。而根据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的说法,这种以“历史主义”(historicisme)和“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régionalisme épistémologique)为特征的“后巴什拉科学认识论”(épistémologie post-bachelardienne)将会导致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后果。
因此,对于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而言,似乎确实存在某种“法国科学认识论”。同时,对于这一家族性的展现,也可以基于那些“来自内部”的证词,即作者们自己的证词。康吉莱姆就总是坚持他和巴什拉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有许多文章是献给巴什拉的,并且,他也系统化了巴什拉的认识论工作。
康吉莱姆甚至还进一步将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的起源追溯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种科学哲学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认识论只能是历史的;第二,这种历史必须是“哲学的”——换言之,是批判的,是被赋予价值的(valorisé)。
同样,福柯也是身处于巴什拉与康吉莱姆的脉络之中。当他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内部划定一条“分界线”时,他区分了“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与概念的哲学。前者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哲学,后者则是卡瓦耶斯、巴什拉、柯瓦雷与康吉莱姆的哲学”。同样,福柯也将这一区分追溯至19世纪,追溯至梅讷·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哲学与孔德的哲学之中。他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归属于第二条脉络之中,并强调这一脉络对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的参与——尽管这一脉络看上去是“最理论化的,在思辨任务中是最具条理(réglée)的”。
无疑,福柯在这里对法国哲学史进行了一个高度图式化的表述。正如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和康吉莱姆这些名字的“并列”,“与其说有助于澄清一种理论状况,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有益处的是去辨别这四个名字各自所特有的独到之处”。事实上,把康吉莱姆和福柯仅仅视作巴什拉的后继者确实过于简化了。康吉莱姆的第一个直觉很大程度上早于他与巴什拉的相遇。而对尼采的解读可能比对巴什拉的解读更能有效解释福柯作品的产生。至于巴什拉的作品本身,无疑是不符合康吉莱姆所提出的“经典”(canonique)解读的。
然而,从这些作者对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的概念来看,我们仍旧有可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虽然或多或少重复了康吉莱姆所提出的公式,但德贡布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家族相似性”的前两个特征。对于法国科学认识论而言,“科学认识论只能在科学哲学中严肃地提出它的问题”。而科学哲学只有“在其采取科学史的形式这一条件下才变得有趣”。
应该补充的是,这一科学史绝不是像其他历史一样的历史,因为它是一部“批判的”或哲学历史(une histoire « critique », ou philosophique)(译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历史-哲学实践”pratique historico-philosophique,不是一种以哲学为素材的哲学史,也不是一种以历史为素材的历史哲学,在其中,历史和哲学面相具有同等重要性。为了区别哲学史,我们将在下文中将这一概念翻译为“哲学历史”)。
最后,如果我们想考察这种方法的后果,我们必须像福柯那样强调,这种法国科学认识论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历史特征进行更广泛的反思:“它不仅向理性思想提出关于其性质、基础、权力和权利的问题,还有其历史和地理的问题”。因此,法国科学认识论似乎具有四个特点。这一认识论从对科学的反思开始,这一反思是历史的,这种历史是批判的,这种历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历史。
如何定性这种“法国科学认识论”,还有待考察。多米尼克·勒库尔(Dominique Lecourt)在向外国传播“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主要代表的论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他们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并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更应该谈论的是一种法国“传统”。这一视角当然有其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阿贝尔·雷(Abel Rey)、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在索邦依次接替前者的教席,并相继担任了科学技术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的主任。
人们还可能注意到,福柯的论文是由康吉莱姆指导的,康吉莱姆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巴什拉,而巴什拉则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阿贝尔·雷。不过,因为并未考虑到这些作者各自的原创性,这样的观点仍然是肤浅的。
如今看来,用“科学思想的风格”(style de pensée scientifique)来描述这些不同作者之间的共同特征可能更为合适。科学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阿利斯泰尔·克龙比(Alistair Crombie)或伊安·哈金(Ian Hacking)为这个术语赋予了含义。当我们谈到“科学思想的风格”,我们就可以指出某一特定时刻出现,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同时也能说明属于这种风格的每个作者各自个性化。
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风格这一概念既有“个性化”的功能,也有“普遍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的“法国风格”。而这也正是康吉莱姆所做的。康吉莱姆强调,孔德通过对科学史的 “哲学概念化”(conception philosophique),成为了“在我们看来,科学史中法国风格的原创性的来源,而且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原创性”。
如果说,人们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国风格”,那么也应该选择出最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作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格的最初体现在了孔德的身上。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者,例如阿贝尔·雷,他给予了这一风格制度上的基础。无疑,我们应该像福柯那样看到卡瓦耶斯或科瓦雷的工作。
我们还可以在这一风格的晚近时期看到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或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作品。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提到那些不是法国人的作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现了这一历史认识论传统的某些方面,如伊安·哈金、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或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得是法国人才能阐明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甚至我们可以说,种风格似乎在法国国外比在法国更富有生命力。
然而在此,我们将局限于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作品,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科学哲学中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最大的关注。我们将特别强调康吉莱姆作品,这既是因为其在历史上处于另外两者之间,也如达戈涅所言,康吉莱姆在由他的老师巴什拉和他的弟子福柯所代表的“两极”之间摇摆,在制度和争论(contestation)之间,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在“理性和尼采主义”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完美地描绘了法国科学认识论所富有的各种可能性,或者说,各种诱惑力。

哲学和科学
当代哲学对科学及其革命的冷漠令法国科学认识论感到愤慨。根据巴什拉的说法,哲学家们并不关心“科学事实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他们并未做出必要的努力来整合同特别是相对论在内的同时代的科学革命。这些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同样的,巴什拉也对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家们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感到失望。当科学家们给出了“哲学上的信仰声明”时,他们总是完整地复述一些并不能反映他们行为地哲学,结果“科学没有它相应的哲学”。
对哲学家而言,他们与科学的距离可以有两种形式。要么是因为他们单纯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无疑可以说明萨特的作品。要么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围绕着科学,阐述一种“清晰、快速、简单的哲学,但却仍旧是哲学家的哲学”。在后一种情况在,问题便是先天(a priori)地说明科学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科学感到任何困惑。
因此,笛卡尔是巴什拉、康吉莱姆还有福柯的一致目标,因为他满足于用“我思”(je pense/cogito)来奠定科学——“在我思中,精神的同一性是如此清晰,以至于这种清晰意识的科学立即成为一种科学的意识,成为了奠定知识哲学的确定性”。
这种态度被巴什拉和康吉莱姆批评为试图“奠基”科学的企图:哲学家“总是试图能一劳永逸地奠定”。哲学试图通过绝对的方式“奠定”科学,以此取消科学的原创性。这种错误的典型乃是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而巴什拉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因此,巴什拉的《近似认知论》(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的最后一章“修正与实在”(Rectification et réalité)正是对梅耶松的《同一性与实在》(Identité et réalité)的回应。梅耶松哲学中“实在论”和“连续论”证明了他对实际科学缺乏好奇心。
事实上,与“实在论”相反,当代科学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给定”(donné),即“给定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它必然参与到某种建构之中”。而针对梅耶松的“连续论”,即认为“科学与常识的态度相一致”的这一看法,巴什拉指出,相对论所开启的“新科学精神”表明,“由此,科学经验就是与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经验”。
对康吉莱姆和巴什拉而言,这种对“奠基”的尝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不是由哲学家预先来决定科学概念的外延”。因此,哲学决不能“先于”科学进行介入,以规定科学的条件。但是,哲学也不应该“后于”科学进行干预,以反思后者的僵直和过时的状态。这就是巴什拉对康德的批评的意义——康德的范畴或物质的概念已经被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或现代化学理论所废止。
与他发展一种“非笛卡尔式认识论”的方式一样,巴什拉在实体/物质(substance)概念上提出了“非康德主义的草案”(ébauche d’un non-kantisme)。这一概念确实“在牛顿科学中发挥了正确的作用”,但它必须“被开放,以便将其正确的功能转化为明日的化学科学”。
因此,哲学既不在科学之前,也不在科学之后,它必须与科学“同步”。哲学必须表现出一种“坦率的现代主义”,并“在新的科学精神的激励之下指导自己”,必须努力做到“真正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思想”。按照康吉莱姆的说法,哲学“必须与科学成为同代人”。
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成为一种“多哲学”(polyphilosophie),就如同为其赋予形式的科学那样多样(pluriel)。巴什拉经常回归科学必须号令哲学这一观念,“科学实际上创造了哲学”,或者说根据另一个公式,“科学指导理性。理性必须服从科学,服从于最新进化的科学、不断进化的科学”。
因此,不应该由哲学来决定科学应该是什么。科学独立存在并构成了科学哲学家们工作的“给定”。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强调,巴什拉是“从具体的科学出发,从这些科学的现象出发……他的认识论正是各种自然科学的真正的现象学(authentique phénoménologie)”。
法国科学认识论不追问科学的基础问题——在这一点上,除了科学自身的历史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威。康吉莱姆如是评价巴什拉:“除了在其自身历史之中的科学(la science dans son histoire)以外,这位理性主义者不向理性要求其他任何的谱系背景或行为正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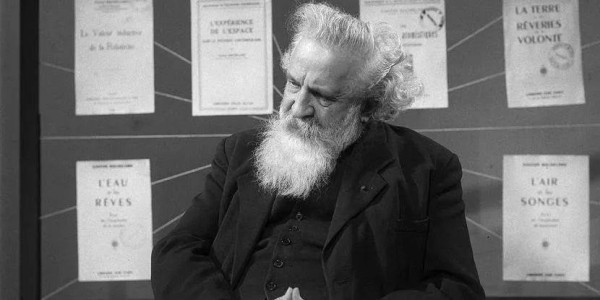
Gaston Bachelard
反对认识理论
只要其是对各种科学而非“一般”认识的反思,科学认识论在其法语含义中就不同于认识理论(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译注:即一般意义,或非法语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
英文术语“epistemology”是于1854年由如费希特一般的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尔(James Frederick Ferrier)所创造,而德语术语“Erkenntnistheorie”则于1862年由哲学史家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所推广,但这些表达都还是认识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
而法国科学认识论则不断明确宣称自己敌视任何认识理论——在孔德批评方法或心理学的各种概念时就已经如此了。在孔德看来,我们不可能“直接”认知“人类精神的法则”,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实际运作的结果,即通过研究科学及其历史来认知这些法则。
阿贝尔·雷也是如此,他在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杂志《泰勒斯》(Thalès)的第一期开篇处指出,“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或口头的辩证法”。巴什拉同样,在拒绝任何方法理论的时候也拒绝了认识理论。而这种拒绝带有反笛卡尔的腔调。正如他在1966年国际科学哲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上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无疑,如今已经不再是《论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时代了。
歌德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写道:‘笛卡尔曾一遍遍写作他的《论方法》。然而,对于如今我们所拥有的而言,它没有任何帮助。’”笛卡尔式方法不再是‘可谓是’(pour ainsi dire),而只是“科学精神的礼貌”(la politesse de l'esprit scientifique)。这种方法既错在其虚假的清晰性,也错在其静态特征。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诸种方法”在不断地运动,总是“身处前沿”,寻求“风险”。
康吉莱姆也拒绝了这种方法的概念。他认为,不存在“一种由一般原则组成的实证性或实验性方法,只有基于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而多样化的应用”。在这一问题上,他引用了巴什拉的话:“各种概念、方法都取决于经验领域,所有的科学思想都必须在新的经验面前有所改变”。康吉莱姆在其他地方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时断言,不可能对科学方法进行一般性陈述:“严格来说,不存在实验性方法”。
从此以后,认识理论的所有经典问题都被法国科学认识论所拒绝——对于传统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尤其如此。在巴什拉看来,不存在比创设式主体(sujet fondateur)更多的给定客体。“客体不能被指定为一个‘直接客观物’(objectif immédiat)”,其在科学的运动中被建构、定义为“各种观念的视角(la perspective des idées)”。
至于科学的“主体”则与一个所谓的创设式我思(cogito)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用“我们思”(cogitamus)来代替这一我思,因为科学的主体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主体。对这一客观给定(donné objectif)的批评也为康吉莱姆所采纳。他坚持巴什拉式“公理”的“范围”,即“客体是观念的视角”。
当福柯用笛卡尔的例子来攻击主体哲学时,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福柯身上发现这种批判。福柯认为笛卡尔应该对“被赋予主体的神圣特权”负责,同时,我们理当看到“一个主体的建构过程是如何横贯于历史之中发生的。这一主体并未被最终决定,也不是真理抵达历史时由此出发的起点,而是在历史内部之中被建构的”。

对科学史的反思
因此,法国科学认识论是对科学的后天(a posteriori)反思。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科学认识论如何能够避免成为科学的简单重复或者简化版本?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科学没有任何补充。
实证主义的风险,或者用阿贝尔·雷的说法是“科学主义”的风险,似乎存在于巴什拉身上——正如康吉莱姆在其中看到的一种“困难”。“一方面,巴什拉离实证主义非常遥远。他并未将他的科学哲学转换为一种哲学科学(science philosophique)。另一方面,当要描述并合法化科学的方法时,巴什拉并没有脱离科学”。
孔德对这一批评做出过回应。他提出,哲学要“系统化”(systématiser)科学。当然,这绝非是法国科学认识论想要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的关系,因为科学认识论与巴什拉一道,提出了一种“分散的哲学”(philosophie dispersée),一种“多哲学”——哲学对于科学没有一种上级功能(fonction de surplomb)——这种功能使哲学对科学进行分类或者系统化。
实际上,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历史方法,才使法国科学认识论不至于只是对科学的简单重复。科学哲学同时也总是一部科学史。不过人们需要理解这一历史方法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在他们提到科学史的同时,巴什拉、康吉莱姆或者福柯都拒绝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
按照康吉莱姆的说法,“如果不参考科学认识论,认识理论将成为对虚空的中介;如果不与科学史产生联系,科学认识论将是它试图讨论的科学的完全多余的复制品”。只有立足于科学史的基础之上,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丰硕成果。也正是在科学史中,法国科学认识论希望能找到诸如科学的客观性或真理与错误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巴什拉指出,“任何科学史家都必然是真理的历史学家”。
我们无疑可以在保罗·唐讷里(Paul Tannery)、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或莱昂·布伦施维克(Léon Brunschvicg)的作品中,甚至在更早的孔德的作品中看到同样的“历史”思想传统。最近有人提出,巴什拉和这些作者之间的断裂可能被阿尔都塞的解释高估了。但至少,科学的历史特征乃是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构成性的特征。
因此,康吉莱姆矛盾地将历史性作为了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虽然历史性通常被认为是与客观性相矛盾的,但在康吉莱姆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是在其历史性中得到证明的。“一门没有历史的科学,换言之,一门在某一时刻,其客观性条件没有受到挑战,并被更为客观的客观性条件所取代的科学——被如此设想的学科不是一种科学”。正是在这方面,真科学与包括占星术在内没有自己历史的“伪科学”相对立。
这种对科学史的关心并非是偶尔的,它是所有这些作者的关注核心。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与英美的科学哲学的对比中格外明显。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前,英美圈的科学哲学选择忽视对“发现的语境”的研究,以便只叩问“证明的语境”,即只关注于使一个理论能被承认为是科学的条件。
但是法国科学认识论所设想的科学史是与传统历史直接对立的。历史学家的首要规则是客观性的律令。但法国科学认识论则宣称,科学史是一部“被裁定的”(jugée)历史。虽然孔德将历史表现为是连续且不断进化的,但“在法国”的科学史则从本质上是不连续的。“哲学史”在黑格尔那里被置入于普遍理性的视点中,而在法国科学认识论这里,科学史本质上乃是一部区域性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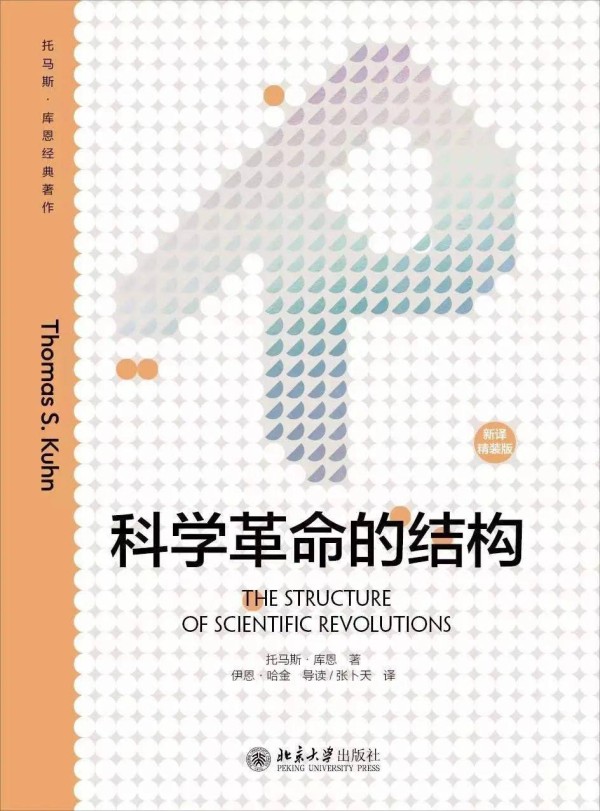
一种“被裁定的”和“复现的”历史
这部科学史不应该是“客观的”,而是“被裁定的”。在“科学史的现状”(L'actualité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中,巴什拉宣称了这一恶名昭著的规则:“与建议历史学家不要进行判断(juger)的要求完全相反,我们必须要求科学史学家进行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将科学史与“帝国和民族的历史”区分开来,后者“恰当地将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作为其理想”。
对康吉莱姆而言,科学史也是一部规范性的历史(histoire normative)。(译注:具有规范性normativité的历史,即能够不断产生新的规范的历史)他认为,“为了理解科学史的功能和意义,我们可以将学校、法院等等对知识的过去或者过去的知识作判断的机构和场所作为模板,并将这种模板与实验室这一模板相对置”。法官即科学认识论——“它被要求通过教授历史以这些科学的最新语言来为历史提供一个判断的原则”。
当然,在这样一种背景中,《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那位尼采同时存在于这两位作者身上。巴什拉就引用过尼采:“在科学史之中,人们必然是要去理解,但也要去判断。在这里,尼采的观点比在其他地方更正确:‘只有通过此刻最伟大的力,过去才会被重新解释’”。
这种判断的想法预设了一种从现在投向过去的目光。巴什拉在《当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活动》(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中提出的“复现”(récurrence)的概念之中,思考着这种现在对过去的回归。在他看来,有必要“制定出一种复现的历史,一种被现在的最终性(finalité)照亮的历史,一种从现在的确定性出发,在过去发现真理的进步形成的历史”。
同样,巴什拉也通过谈论“顶部对底部的反应”,现在对过去的反应来说明“复现”这一概念。正是以科学的现状和“新科学”(science fraîche)的名义,科学的过去得到了裁定。因此,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才是根本。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希望原初之处总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公理”必须被反对。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重构并重新排列了科学的过去。“现在”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科学认识论的某些特点,但也引起了某些的困难。
例如,“现在”的重要性使我们能够理解康吉莱姆所实践的科学史的准政治性格(caractère quasi politique)。人们常常对他的科学史研究中明显的,特别技术性的特点感到惊讶。实际上应该强调的是,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理由,而这解释了他的叙述中常常可见的高度论战性特征。
如果说康吉莱姆选择研究反射概念的形成历史是为了在巴甫洛夫反射学和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抨击那种认为生命只是对环境影响进行回应的机械论式生命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康吉莱姆在《反射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的导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这是一个拯救人的自主性(autonomie)的问题,是“无论真假,人赋予人的生命的杰出尊严……尊严的本质是命令的权力,是意志”。当然,同样的解释在说明“什么是心理学”(Qu’est-ce que la psychologie ?)这一科学史的战斗片段时更加有效。
“复现的历史”这一观念,与英美圈所说的历史的“辉格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这一观念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将科学史中的“法国风格”与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对库恩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科瓦雷的工作并非是将科学思想史中的某一时刻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加以裁定,而是要去描述这一时刻显现给其主人公的样子。在科瓦雷看来,科学思想史旨在“将所研究的作品置于其知识和精神环境中,以其作者的心态、偏好和厌恶来解释这些作品”,从而“像研究成功案例一般仔细研究错误和失败的案例”。
但是,这一复现的概念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困难。第一种风险是通过展现现在的真理的方式来重构过去。如此以来,我们就会落入康吉莱姆所反对的“科学家的历史”之中。这种历史出现在诸如科学教科书的序言或“历史摘要”之中,它在过去就看到了现在的真理,从而允许科学家们“在现在暂时无法正当化自己的发现时,可以在过去之中将其正当化”。
康吉莱姆同样还谴责了寻找“先驱”(précurseur)这一广为流传的错误。这种“先驱病毒”将是“没有能力面对科学认识论式批判的最明确的症状”。这种寻找先驱的做法使人无法把握历史上真正的新奇事物。“如果存在着先驱,那么科学史将会失去所有意义。若非如此,科学本身将只在外观上具有历史维度”。这将阻止我们理解一个概念在特定系统或时期之中的含义——当我们把拉马克视作达尔文的“先驱”时,我们将既无法理解达尔文的原创性,也无法理解拉马克的一致性。
这种“先驱”概念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先驱“将是一位身处好几个时代中的思想家,这个思想家既处于自己的时代中,也处在那些被认为是其后继者的时代之中”。这一概念也假设了历史是线性的。它是一种独特的“竞赛”:“一位先驱将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者,这位先驱曾经跑过了另一个人在新进跑过的一段赛道”。然而,我们绝对无法确定这是同一条赛道。
巴什拉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并指出,“需要一种真正的策略来处理这些可能的复现”。然而,当他在科学史中看到“知识的理性联系进步”史或“非理性主义的失败史”时,巴什拉可能并没有完全摆脱与“科学家的历史”相伴生的进步意识形态。对于“复现”这一概念的风险,康吉莱姆可能比巴什拉更为敏感。他承认自己对机械地运用复现理论有所保留,并宣称一种“复现的善用”——“认识论复现的历史方法不应被视作万灵药”。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复现概念无疑与巴什拉所处理的领域,即数学物理学领域和计算合成化学(chimie des synthèses calculées)领域密切相关。
这种复现的历史所产生的第二个困难是,它使任何科学史都是绝对暂时的。巴什拉认识到了这种“毁灭的要素”,并认为其来自于“科学的现代性的短暂的特性”。每一种新的重要发现都会使科学史必须被重写。巴什拉坦率地假设了这种“相对主义”的后果:“科学的每一次成功都会纠正其历史的视角”。
然而,按照他的说法,却也存在着一种“已经过时的历史和由现在仍旧活跃的科学所许可的历史之间的辩证法”:某些理论(例如燃素说)绝对是已经过时了的,因为它们立足于一些“基本错误”,而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约瑟夫·布莱克的热质说,“即使它们包含需要重新加工的部分,也是在测定比热的实证实验中出现的”。
康吉莱姆也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他所写的反射概念的历史包括了“反射概念沿革史的历史(histoire de l’historique du réflexe)”这一基本要素。而在其他地方,康吉莱姆则欣然承认,他自己关于生机论的工作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现而部分失效,他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写作。
复现概念带来的第三个困难是“过去”这一词本身的定义问题。这段历史本身似乎是被重构的,而不能被认为是给定的。康吉莱姆指出,“绝对地看,‘一种科学的过去’(passé d'une science)的概念是一个俗常的概念。过去是回溯性质询的各种大杂烩”。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科学的过去指的是编年史以外的其他某种东西。科学史的节奏因不同时期的强度或其所研究的领域的丰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科学史时间不能只是一般时间长流的支流……在一般历史中的同一个时期内,不同学科中的科学真理的出现的时间,对科学真理的验证的时间各自有着不同的流动性与粘性”。科学认识论对过去的这种重构为科学史开辟了广阔但危险的前景。康吉莱姆引用了苏珊娜·巴什拉(Suzanne Bachelard)的话:“[科学]史学家在一个理想的时空中构建他们的对象。他们也有责任避免这一时空沦为妄想(imagina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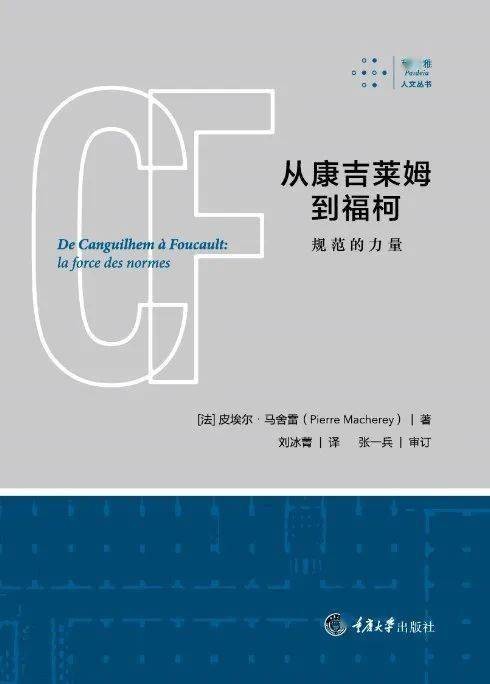
不连续性与“断裂”
不连续性也使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与经典意义上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不同。相较于“连续主义”历史,法国的科学史是一部不连续的历史,是一部“断裂”(rupture)的历史。这一解释无疑被阿尔都塞的巴什拉解释所加强。
虽然“断裂”这一概念被阿尔都塞的解释转化为了“认识论的切断”(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并被激进化,但它仍然是法国的科学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少在巴什拉和福柯那里仍旧如此。另外,我们还应该指出,科学史发现的这些断裂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断裂,也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断裂。法国的科学史是一部断裂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知识“区域”或“大陆”的历史。
人们通常认为,法国科学认识论的这种不连续性是与迪昂或梅耶松的“连续性”相对立的。对康吉莱姆来说,这也是与孔德的进化主义科学史保持距离的问题——孔德的进化主义科学史并没有为任何真正的新颖性留下空间,在起点处,一切就已经是“萌芽状态”。
康吉莱姆明确批评孔德,“人性(humanité)的历史……经历了转变、蜕变,但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危机,从来没有断裂和创新”。在康吉莱姆看来,科学史“必须作为历史而不是科学来写作,作为冒险而不是展开(déroulement)来写作”。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尼采的身影。尼采反对那种试图寻找延续性,“只想保存生命”却“总是忽视处于生成之中的东西”的古板历史。相反,他主张一种允许做出“有利于新事物的有力决定”的谱系学。
在巴什拉看来,科学史的特点首先是“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之间的断裂,永久的断裂”。尤其是“新科学精神”,它从根本上与日常经验相抵触,而梅耶松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当代恰恰完成了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之间的断裂”。科学不是“经验的同义叠用(pléonasme)”,科学现象是理论与技术建构的复杂结果。任何科学思想的真正进步都“不仅是对俗常知识的改革,还是一种转换”。
根据这一公式,我们似乎可以将其视作是传统的为对感性经验进行贬低的柏拉图式解释。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巴什拉同时强调了这种感性经验的丰饶性。正如巴什拉考察的想象力资源的“诗性”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巴什拉对感性经验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剥夺。
巴什拉以一种更具原创性的方式表明,科学内部的进步是相继产生的科学理论之间的“革命”、“断裂”或“变异”为其特征的。“即使在某一特定问题的历史演化中,人们也无法掩盖真正的断裂、突变这些破坏认识论连续性的论题”。他对数学物理学的兴趣使他强调了这种断裂。巴什拉用“认识论行为”(acte épistémologique)的概念来指代这些“科学天才们的震颤,这些震颤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福柯采纳了这种不连续的观点。他指出,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方法”,因为科学史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断裂现象”上去了。他明确提到了巴什拉。“在他对科学史中的不连续性的反思,以及在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这一观念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我反复使用的要素”。福柯的“考古学”不同于“观念史”。“考古学”想要讨论的是“切断、裂隙、裂口、实证性(positivité)的全新形式以及突然的再分配”。
康吉莱姆对于断裂可能并不那么敏感。在他所关注的生物学和医学史中,确实很难看到真正的断裂。因此,他更倾向于去思考历史上的人物的作品中独特断裂、“一连串的断裂或部分的断裂”以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走得很远。因为他对诸如哥白尼革命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具有的断裂特征提出了质疑——甚至“哥白尼革命和伽利略革命也都留下了一些遗产”。
或者说,在一种整全的视野之中,他试图超越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对立(这种断裂可能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断裂的认识论适用于科学史上的加速期……,而连续性的认识论则在知识缓慢的开始或觉醒之中,寻找自己的偏好对象”。
相较于标记断裂,康吉莱姆更乐于寻找“亲缘关系”(filiation)。比如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他就试图证明反射概念的真正“生父”是生机论者的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而非机械论者笛卡尔。“科学史,其首要义务便是承认那些确实是生父之人为生父,即使有别人被判定为更值得占据这一位置。

Georges Canguilhe
“认识论的障碍”和错误
自其学位论文起,在巴什拉的思想中,对认识论断裂的存在的观察便占据了首要位置。正如康吉莱姆指出的那样,巴什拉直到“后来才发展出了能够说明这些问题的哲学概念”。断裂意味着需要打破一些东西。这种必须被打破的东西就是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障碍”(obstacle épistémologique)。
“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来提出科学认识的问题”。根据巴什拉的说法,这些科学认识的障碍内在于认识之中。“正是在深刻地认知这一行为中,基于某种功能的必然性,迟钝与麻烦逐渐显露”。这种关于人类思想中固有障碍的想法使我们回想起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新工具》中所描述的“部落的偶像”。
康吉莱姆与福柯后来都对巴什拉用心理学或人类学术语来描述这些障碍一事表达遗憾。在《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巴什拉列举了现代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诞生时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由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图像构成:植根于日常经验、语词障碍(一个词或一个图像构成了解释),实体论或实在论的障碍、重视生命的泛灵论障碍、精确度的过度(excès de précision)。所有这些障碍都不是纯粹的剥夺,但它们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丰饶性——特别是从想象与诗性的角度来看。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巴什拉提出了一种“客观认识的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其实际上首先是一种“知性的净化”(catharsis intellectuelle),或者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改革”,以及,根据《应用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appliqué)的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是一种“自我的知性监视”。
然而,这种障碍的概念并不是纯粹负面的。障碍对于思想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思想需要通过与障碍的对抗来构成和形成。巴什拉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坚持“否定”(le négatif)的肯定性(positivité)——人必须“通过破坏来创造”。
因此,错误(erreur)的概念也具有相应的重要性。在各种意义上,它都是优先于真理的概念。错误在时间上是第一位的,它总是已经存在的。“真理不可能居于首位,错误才是首先的”。科学认识正是为了与这种首先存在错误而形成的。“科学认识总是对幻相的改革”。正如作为诗人的巴什拉所言,“初生者并不纯洁”。
康吉莱姆也坚持“错误的理论首要性”,因为他把这作为巴什拉的认识论的“第一公理”。对康吉莱姆来说,至少在其初始处,认识总是不纯净的。他甚至承认科学认识始于神话:“科学理论及其作为自身解释原则的基本概念是嫁接于古代图像之上的——如果说这个词今天还没有贬值的话,那么我们将这个古代图像成为神话”。“‘原生质’(plasma initial)难道不是产生出一切生命的神话液体的合逻辑的化身(avatar)吗?难道不是维纳斯自其中诞生出来的泡沫吗”?
后来,康吉莱姆越来越多地将科学认识的障碍设想为社会或政治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阿尔都塞和福柯那里借来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在1970年代形成了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按照他的说法,使用这一概念乃是“一种更新而不拒绝巴什拉的教诲的方式……无论我的年轻同僚们是如何对其自由发挥的,他们确实都受到了他的教诲的启发和加强”。
康吉莱姆将科学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紧盯着(loucher)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承认这种科学的威望,并试图模仿其风格”。科学史一方面要把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分离”,“主张并包含真(l'authentique)驱逐非真(l’inauthentique)这一关系的历史”。但它也必须将科学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避免“将一种科学的历史还原为沿革史的陈词滥调,或者说一幅没有立体阴影的平面图画”。
和巴什拉一样,在康吉莱姆这里也有一种真正的“否定”的肯定性。科学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它不单单只是幻相,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具备肯定性功能。因此,生机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表达了生物学自主性的合法要求——生机论使我们注意到“关注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于野心勃勃试图吞并其他学科的物质科学的独立性的一切生物学”。
科学意识形态也有预测的功能,是科学构成的“可能性条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新科学认识的逐步产生,都要求某种智力冒险对于合理化的先行性,要求一种自信的越界。这一越界基于生命和行动的需求,以审慎和不信任的态度超越了那些已经被知道和验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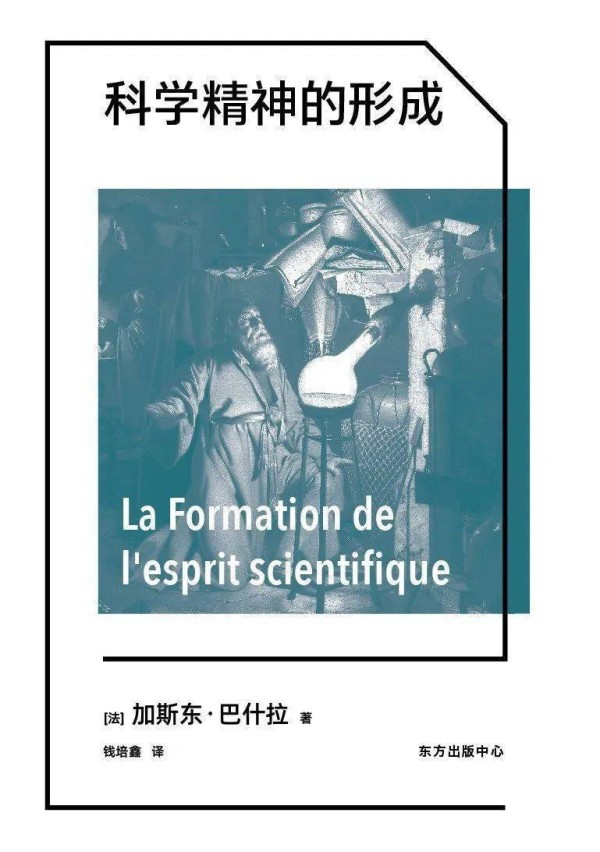
“各种区域理性主义”
正如历史认识论以时间上的断裂为其特征,它也以空间上的中断为标志。巴什拉合康吉莱姆都认为,根据学科以及知识的“区域”的不同,科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结论是由巴什拉得出的,他毫不犹豫地谈到了“各种区域理性主义(rationalismes régionaux)”(译注:以下直接表达为区域理性主义,但都是复数的),在“知识的合理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区域”。
同样,巴什拉在《应用理性主义》中研究了一种“电气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électrique)或“机械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mécanique)。针对有着“统一狂热”的理性主义,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将理性主义切分开来,以便将其与其赋予形式的物质、调节的现象、创立的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相联系起来”。
同时,巴什拉也认为,区域理性主义被赋予了某种整合的力量:“在所有区域理性主义中,都有一个一般理性主义的萌芽”。伊波利特正确地指出,巴什拉谈到了“不同的建筑、理性的不同领域——通过类比胡塞尔所谓的区域本体论”,因此他拒绝采纳一种“整体性的哲学”。
康吉莱姆也用过这种地理隐喻。他指出,为了描述历史认识论的特点,我们要看到“与科学哲学相反,它是一种特殊或区域性的研究……对科学的各种原则、方法以及结果的批判性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除了应用理性(raison appliquée)的部分,没有哲学批评。而所有的应用则必然是区域性的”。
凭借一系列的空间隐喻——边界、位移、概念的输入和输出——康吉莱姆能够描述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意识形态相较于科学未来将要占据的位置是处于被“驱-逐/未-抵达”(dé-portée)的状态。“当一种科学来占据似乎由意识形态所指明的地方时,意识形态却并不在人们所预料的地方”。
至于福柯,他把《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作为“严格的‘区域’研究”,把“考古学”作为“总是有限且区域性的比较”。相较于历史研究,他特意将这种空间研究加以特权化。这是一个绘制“考古学领土”和描述“与其说是我们各种科学的源起(genèse),不如说是这些科学特有的认识论空间”的问题。
阿尔都塞也采用过空间隐喻,并将其激进化。他在《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中提到过科学“大陆”:“如果我们考虑过人类史上的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当作是各种区域形成,与我们将称之为伟大理论大陆的东西联系起来”。“两片大陆”,即数学和物理学,通过泰勒斯和伽利略向科学认识开放。而马克思将开启“第三片大陆,即历史大陆”。正如阿尔都塞更喜欢切断而非断裂一样,他更喜欢大陆而不是区域,因为大陆的这种隐喻突出了一种切断的观念,而区域的隐喻却没有。
这种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多元性,似乎与科学的多样的,不可缩减的复数性特征相一致。统一,或对统一的寻求,将是一种在错误意义上本质的“哲学”特征,而正如英美圈的作者常说得那样,科学总是“不统一”的。
而这正是康吉莱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他将孔德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置,而前者对各种科学分类中的“不可还原性”极为敏锐。与科学哲学相反,康吉莱姆的认识论因其自身乃是一项区域性的研究而感到自豪。科学哲学“以知识的统一为目标”,“尽管不是没有危险,但它可以将自己扩展为一种认识理论”。

Louis Pierre Althusser
理性的历史和地理
由这些作者所发展的新认识论使得他们对理性的生成展开了反思,而理性只能通过科学来认识。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则倾向于使理性的形式依赖于历史或“地理”条件。因此,巴什拉解释说,由于“理性必须服从科学”,它必须遵循那些“辩证法”——“那种认为理性是绝对和不变的理性的传统教条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过时的哲学”。巴什拉提出的新理性主义或“超理性主义”(surrationalisme)仍旧有待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论争对于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philosophie)来说显得非常陈旧。
福柯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参与到这种论争之中——“扮演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阵营中任意一种无聊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关于理性的历史性的教诲,并承认他“受益于”巴什拉关于“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的观念。这是一个“确定理性的形式的问题。这种形式被表现为主导形式,并被赋予了理性的地位,以便使其作为合理性(rationalité)工作的可能形式之一出现”。
福柯拒绝了“在对理性的和合理性的历史的进行任何批判或者批判性质疑时经常出现的那种威吓”(译注:指要么接受理性,要么陷入非理性),他认为我们可以考察“合理性的偶然历史”,正如我们可以进行“对合理性的理性批判”(critique rationnelle de la rationalité)。
如果说,福柯多次回到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运动?”(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向理性提出“它的历史和地理,它的直接过去和它的行使条件,它的时刻,它的地点和它的现在性(actualité)”的问题——合理性虽然总是宣称自己是普遍的,却也知道自身在历史上被决定的各种形式。
同样,理性也是由其应用领域所决定的。因此,康吉莱姆将“传统的法国理性主义”,即基于数学科学的“清晰观念”的理性主义,与植根于生物学的“生机理性主义”区分开来,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定义:“如果说,理性与其说是一种把握包含于事物或精神的实在之中的本质关系的统觉能力(pouvoir d’aperception),不如说是一种在生命经验之中建立规范性关系的制度化能力(pouvoir d'institution),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说,我们也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认同巴什拉先生在《水与梦》(L'eau et les rêves)中的优美公式:‘理性主义者?那是我们努力想成为的人……’”。
在1947年的“关于生物哲学的笔记”(Note sur la philosophie biologique)里,康吉莱姆就已经在对同时代生物哲学的批评中,唤起了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在我们看来,对某些哲学态度的剧烈谴责是与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相关,而非与理性的普遍性相关”。
在福柯看来,这种理性的空间化也使得我们可以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起更清晰的联系。“只要当我们可以用区域、领域、植入(implantation)、位移、转移这些术语来分析知识,我们就能掌握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发挥功能,并继续其效果的过程”。正是围绕着这种空间表现,福柯著名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联系被编织出来了。
从真理到诸规范
福柯并未停留在对理性的历史性的简单考察。因此,他多次强调,阅读尼采让他知道了“光是书写合理性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书写真理的历史”。因此,福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相较于去问说一种科学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使它更接近真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说,真理所包含的话语、知识与真理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是不是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历史”?《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提出的正是关于“求真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的历史的轮廓。
对真理的类似质询也出现在康吉莱姆这里。他是一位“无证尼采主义者”(nietzschéen sans cartes)。在他看来,科学真理不反映任何客观性,而是科学陈述/命题(énoncé)本身的历史及其一连串的修正。“科学的真言性(véridicité)或说真话(dire-le-vrai)并不在于忠实地在生产某一从最初就被刻在物或知性中的真理。真,乃是科学言说(dire scientifique)中被说出来的(le dit)。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真呢?“靠的是其原先从未被说出来过”这一观念,导致康吉莱姆将真理定义为一次决断、一个事件。“在数学之前——在构成数学的一连串的发明和决断之前,不可能有数学的定义”。这不仅适用于数学,也适用于科学史的其他领域。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康吉莱姆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科学判断都是一个事件”。
因此,康吉莱姆只在科学话语的历史中提出真理的问题。“一种科学是由它的批判性修正所规范的话语”,而真“不是一个在前面的-位置/命题(pro-position),而是一个规范性的预先-作为基础的-位置/前提(pré-sup-position)”。科学史对过往的陈述/命题总是不断表示质疑,并对其话语进行不断重组。可以肯定的是,康吉莱姆的这种科学史概念只能从他的生物(le vivant)概念中来理解,而他的生物概念则是由其规范性特征所定义的。
在他的经典作品《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康吉莱姆解释到,“生命实际上是一种规范性活动”,它“建立了规范”。就科学是人类这一生物(le vivant humain)的表达而言,它们也具有这种规范性能力的特征。科学史就其本身而言是规范性的,就像生命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样。
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在生命之中扎根发芽,对人类意识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规范性将无法解释”。当他借用生物学术语“形成/发育”(formation)和“变形/畸变”(déformation)将科学史定义为“科学概念的形成、变形和更正的历史”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生物学在康吉莱姆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但在将科学与真理视作同一的同时,康吉莱姆与尼采一样,也认为科学是诸如艺术或道德等等其他人类这一“生物的活动”中的一种,“在哲学判断方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特权”。在他最具尼采风格的文章“论科学与反科学”(De la science et de la contre-science)中,康吉莱姆指出,存在着“来自于科学的选择以外的选择可能性”。科学并不具有必然性的特征:“矛盾律并不强制导致科学的构成”。
因此,他得出结论,就像美或善一样,真理是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一个“比真理更一般的术语”,而且,“真理并不是人类可以拥抱的唯一价值”。康吉莱姆在这里明确提到了尼采和他的“真理的价值论偏见理论(théorie du parti pris axiologique pour la vérité)”,尼采“从未停止过将真理作为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在这些问题上,康吉莱姆似乎还受到了尼采的另一位细心的读者,马克斯·韦伯及其关于“价值多神论”(polythéisme des valeurs)的评论的启发。
这种认为科学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的观念促使康吉莱姆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意味的公式,例如“不存在哲学上的真理”,因为“真理的价值明确只能适用于于科学认识”。或者肯定说,“‘真认识’(connaissance vraie)”、‘科学认识’(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或者‘科学和真理’都只是一些冗词(pléonasme)”。
面对他的哲学家读者们的讶异,康吉莱姆自我解释并说明,只有科学真理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哲学是一个没有其有效范围的游戏”,并不是认为哲学没有对象。哲学的功能是在各种价值之间,在科学、美学、道德或政治这些价值之间进行仲裁。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在哲学这里,科学的真理与其他价值(如美学价值或伦理价值)相互对抗。
“哲学价值”是“一种观念,一种整体的观念。在其中每一种价值都会相对于其他价值处于各自的位置”。但康吉莱姆的结论是:“以上……也许说得不是很清楚”。在康吉莱姆看来,巴什拉文本中“合理性意识”和“诗人的创造性意识”是否共存并不清楚:巴什拉仍然“对这种成功的配置(économie de cette réussite)保持着完全谨慎”。
同时,康吉莱姆拒绝了可以从他对“真”的定义中得出的相对主义后果。在他看来,一种规范性话语、一种科学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话语之间是有区别的。正是这一规范问题将康吉莱姆的认识论与福柯或库恩的认识论相互区分开来。
康吉莱姆在他对《词与物》的评论中指出,“在今天,没有一种哲学比福柯哲学更不具备规范性”:“就理论知识而言,是否有可能只在其概念的特殊性中,而不参考某些规范来思考它呢”?同样,康吉莱姆批判库恩忽视了“哲学批判”的概念,并只停留在了“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尽管库恩使用了“正常科学”(science normale)一词,但他却忽视了“各种特殊的科学合理性”。
然而,在相对主义这个问题上,康吉莱姆似乎也可以受到与福柯相同的批评。当英美圈的读者攻击福柯的相对主义时,他们积累了一定量的,可以用于针对整个法国科学认识论的反对意见。但是,反过来说,当其他评论家为在“理性的”意义上解释福柯这一观念进行辩护时,他们同时也在“拯救”历史认识论。
根据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或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说法,福柯是一名“相对主义者”,而且在普特南看来,福柯更具危险性,因为他是精巧而有文化的。而在罗蒂看来,福柯是一名“极端相对主义者”,一名尼采主义者,他想“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对大写真理的统一性的直观”,“对他而言,真理隶属于权力”。
最后,查尔斯·泰勒(Charlers Taylor)认为,福柯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禁止任何解放行动,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实践后果:“因此,以‘真理’为名的解放,只有通过用另一种权力制度取代这种权力制度来实现”。同样,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把法国科学认识论者看作是理性毁灭的使徒:“在其最激进的版本中,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可以支持逻辑学的多元论:每一种科学,或者如阿尔都塞所言,每一片科学‘大陆’,或者像福柯那样说,每一种认识型(épistémè),都有其各自的逻辑法则与推理规则”。
然而,我们也有可能以某种具有可信度的方式支持另一种观点。我们可以和加里·古廷一样,认为福柯的考古学“不是摧毁了所有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要求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工具”,而是留下了“客观真理的实质性内核”。福柯的怀疑论只涉及那些他认为“可疑”的科学。福柯承认,“如果我们向理论物理学或有机化学这样的科学提出它们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我们是不是提出了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甚至不需要被视作问题。医学本身“确实拥有比精神病学有更强的科学结构”,反对那种“禁止围绕个人产生科学话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律法”,甚至还提供了一种个体科学(science de l’individuel)的模板。因此,福柯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科学史家,而不再是一个“极端的先知”。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这当然是一种“语义通缩式(déflationniste)的解释”,但它至少很适合解释福柯早期的“考古学”工作。
在这方面,他最好的作品《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尤其如此——该书明确内在于历史认识论的法国传统之中,并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作《正常与病理》的一种历史补充(au Normal et au pathologique)。(译注:斜体的书名很明显是康吉莱姆《正常与病理》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其定冠词le与介词à缩合后变成了au,所以变成了auNormal et au pathologique,但并未感觉这种表达有何深意。)
同样,伊安·哈金也提出了一种合理解释。他在福柯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对康德问题的历史性重提:福柯的考古学是“历史化的康德,但是以巴什拉而非黑格尔的方式历史化的”。这无疑是“历史先天”(a priori historique)这一矛盾且诡秘的概念的含义。福柯解释道,考古学分析是“一项努力探索认识与理论是何以成为可能的研究……在哪种历史先天的基础上,在哪些实证性的要素中,各种观念得以显现、科学得以构成、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理性得以形成,以便它们很快就解决和消失”。
伊安·哈金本人则延续了福柯后来的“谱系学”研究——他解释说,人类科学的各种门类具有“塑造人”(façonner les gens /making up people)、改变现实的效果,因此它们是一些直接有效的科学(science directement efficace)。然而,与此同时,伊安·哈金还解释说,这些“知识”并没有被还原为“权力”:通过他对“记忆政治”(mémoro-politique/ mémoro-politics)研究,伊安·哈金旨在证明“生命政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认识既是、也不是一种权力”。因此,我们无疑是可能利用法国科学认识论的工具来书写一部并不必然导向相对主义的概念史的。

Michel Foucault at Vaugirard Apartment, Bruce Jackson©,1975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三人的科学哲学尽管具有风格上的共同性,但互相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着重反思的是不同的科学。巴什拉的断裂和障碍的认识论与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相关。非欧几何、相对论和量子革命在现代科学与过去的科学还有常识的表述之间,引入了真正的断裂(césure,译注:诗歌的顿挫)。巴什拉并不掩饰他受到“一种典范科学的历史,即数学的历史”的启发。他的理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数学理性主义。
而在生物科学史,也就是康吉莱姆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则很难找到“一些与相对论物理学或量子力学那样具有同等级革命性效果的概念断裂”,甚至可能连达尔文主义都不具有这种意义。而在他更加关注的医学科学史中,康吉莱姆注意到了科学与技术的交织,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乃至伦理问题之间联系。他的理性主义以规范问题为中心,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生机理性主义”。
最后,福柯从未宣称过自己是要处理人类科学以外的东西。而这些学科还尚未“跨过形式化的门槛”,并且对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产生反馈效果,甚至还会对这些对象起到构成效果。
这三位思想家的例子让我们想到,每一种科学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推理(raisonnement)风格,而且还诱发了某种科学哲学的风格。
注 释
见文中。
相关文章
巴什拉|火与敬重:普罗米修斯情结
巴什拉|圆的现象学
巴什拉|想象与物质
福柯|生命:经验与科学
福柯 | 精神疾病的历史构成
福柯 | 疾病与存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