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莫言与朱之文,都是山东人,山东人在生活中给老百姓的印象之好,如果说在全国各省排第二,哪个省可以排第一?憨厚老实、豪爽热情、乐于助人,简直就是山东人的标签。大家还记得那个疫情期间送菜的大车司机李保民不?“人家有钱出钱,没钱我出力可以吧”,直接而本能的一句话让全国人为之泪奔。

但是轮到朱之文与莫言却大不一样了,先说朱之文吧,一个老实巴交,既无文化又无貌相,既无家产又无背景,土到掉渣的农民,全凭自己对唱歌的挚爱,混出了人样。凭良心说,他何错之有?但是却引起那么多嫉恨,各种粗俗的话语、各种丑陋的拼图,越来越充斥网络。

如果说,很多人嫉恨朱之文,是因为他没有文化,太低级造成的。那么莫言可是世界级文豪,但依旧饱受上至专家下至黎民的诟病。分析起来似乎各有各的原因,但是小编认为其中有个最简单的也是他们共同的原因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他们都是山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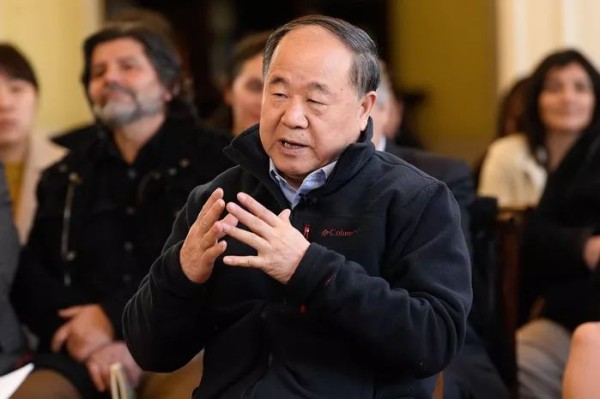
山东人一个共同的性格造成了莫言与朱之文今天四面楚歌的舆论局面。什么性格呢?三个字:特老实!
朱之文因为老实,所以借钱给老乡,因为老实所以被别人踹门,也因为老实本分,宁愿住在农村,不舍一亩三分地。但是这些在很多人眼里,却不是老实,而是作秀与狡诈。因为一般人飞黄腾达之后会高高在上,远走高飞,纸醉金迷。朱之文违反常规,于是他们断定:这是作秀。

而莫言照样也是因为老实,不识时务不识时务,家丑国丑一个劲地往外抖,不会花言巧语,不会吹捧奉迎。吃煤也不嫌丢人,还说给外国人听。自己不要面子,也不顾及他人面子,不理解一些爱面子的同胞的感觉。

小编是与莫言是同一时期的过来人,看过莫言的《黑血》《黑沙漠》《红高粱》《蛙》,不过跟批评莫言先生的人感觉不一样,他们认为莫言写的、以及说的,太过夸张了。小编却觉得,他非但没有夸张,反而很多地方还做了美化。很多更甚的东西完全没有写出来。那时候发生的、而现在人不信的事,多如牛毛,岂能以扇个耳光和吃块煤来形容,这样的芝麻小事那时连皮毛都不算。但是前人不说,后人不知,这就是造成今天的年轻人,不相信自己祖先经受苦难的现实。他们不知道今天的生活,是老一辈如何熬出来的。现在都难以置信了,再过十年百年,是不是更认为那是天方夜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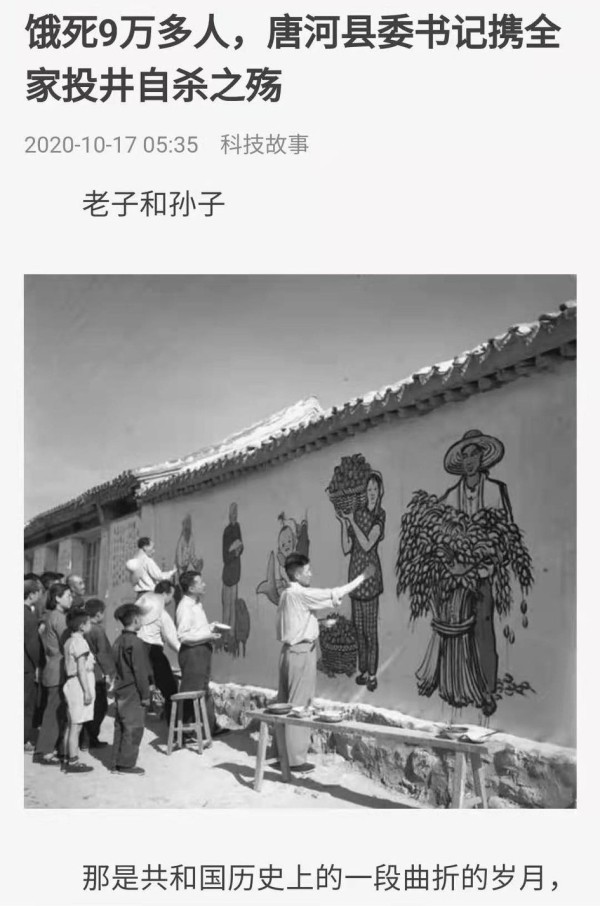
有些人喜欢打着民族和爱国的大旗,对文学斥三喝四,喜欢站在政治的角度看待文学。王蒙先生对此表示愤怒,认为那是悲哀的,文学应该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而莫言曾经说过:我写文学是站在人的角度,带着对弱者同情的态度。
其实,关于政治立场,国家同意出版,还给他颁奖了(莫言几乎每一部国际获奖作品,都是先在国内获奖),说明他这方面肯定没有问题的。司马南是把莫言文学上纲上线的最主要代表,不过,他的好友即《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却不容忍他,要求监管部门对这些“宵小”言论加以管控。

著名评论人老梁认为“莫言是一个敢作敢为敢说真话的人,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中国固有的文人相轻,才引起不少争议。”“敢说真话”正是山东人的优点,令人遗憾的是,在莫言与朱之文身上,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弱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