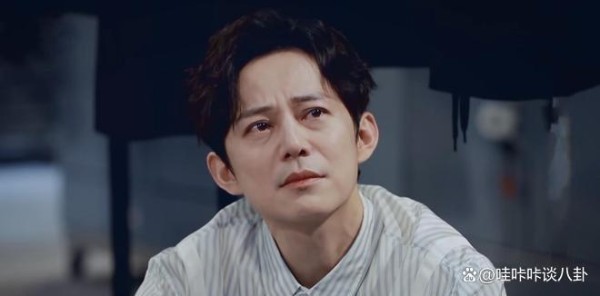Chapter3 云泥有别乔维安最新章节
早上十点,百叶窗遮住了楼宇之间明媚的日光,李明啪的一声合上最后一张简报,高层的早间会议结束,赵平津推开椅子,守在外面的秘书小董已经进来,压低了声音请示:“赵先生,保达公司的徐总已经到了。”
赵平津点了点头站了起来。
助理涌上来,忙不迭地收拾桌面的文件和材料。
沈敏跟着赵平津往办公室里走,赵平津忽然回头,淡淡地说了一句:“找个人把横店那屋的煤气水电费交齐了。”
沈敏愣了一下:“小黄同志连水电费都不缴?”
赵平津不自觉地皱眉头:“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沈敏立刻道:“我亲自去办。”
沈秘书转过头去,脸上是忍俊不禁的笑意,老板这是……心疼?
赵平津回到自己办公室,一工作就是一天,直到秘书下班前来提醒他晚上的应酬时间,他又看了一眼手机,沈敏应该已经知会了她,她从来不会给他打电话。
一个女人无情无义到这份上。
他按了按发晕的脑袋,闭着眼躺在沙发上。
黄西棠比他清醒百倍,她在横店的生活根本与他再无任何关系。
这么些年来他来来回回地在京沪两地跑,他一向若是到南边来,基本所有的工作应酬都只是在上海,以前有过这种饭局上带出来应酬场面的女明星,即使正在横店拍戏,若是得了经纪公司安排,哪个不都是急如星火地赶回上海来,他真是昏了头,才会千里迢迢去一个破烂小镇看一个不成气候的小女明星。他一把将手机扔在了地上,除了北京,他哪儿也不再去。
七月中旬,高家新来了个厨子,于是几个男人携家眷在高积毅家里吃饭。
他们一块儿在同一个大院家属楼里长大的几个发小儿,年纪稍长的高积毅和方朗佲已经结了婚,赵平津虽说跟郁家的姻亲关系定是定了,可还是混世魔王样儿,剩老幺陆晓江,打小就是个乖孩子,跟在他们几个调皮捣蛋鬼后面,一副书呆子模样,在国外硕博都读完了,刚刚回国在一家国资银行做投资分析。
于是近年来大家都回归家庭生活,饭后也不出去了,高积毅整了一套丹麦顶级音响,放在客厅里,女人们却用来看电视。
旁边是一个茶厅,老高在一旁泡茶,陆晓江坐在一旁一罐一罐看他那些好茶,赵平津和方朗佲聊天。
方朗佲笑着挤眉:“舟舟,前段跑上海跑得挺勤啊,怎么最近不去了?”
赵平津跷着腿靠在椅子上吸烟:“怎么了?”
高积毅兴致勃勃地道:“你小子单了有一阵子了,不是真准备结婚前修身养性了吧?”
赵平津有点烦躁地熄了烟:“甭提那事儿。”
陆晓江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插了句话:“瑛子姐挺好的,我回来前在洛杉矶见过一次,更漂亮了。”
赵平津皱着眉头,没有搭话。
高积毅捅了捅他的肩膀,带着过来人的语气:“结吧,迟早的事儿。”
高积毅现在的老婆是第二任了,刚给他生了个儿子,年纪比方朗佲的媳妇儿青青还小一点,孩子有保姆带,她依旧每天美容购物,日子过得比婚前还舒心。
客厅沙发上,女人们凑在一起聊天看电视,晚上八点多,影视台在放颁奖典礼。
忽然间客厅里熟悉的旋律响起。
只听到高积毅的老婆对着屏幕雀跃地叫了一声:“啊,这男的是谁?”
青青轻声地答:“是江超,我以前好喜欢他。”
女人们忽然停止了交谈。
一个男明星在台上唱歌。
高大的男人,梳油头,穿白色西装,还是相当有魅力的男人。
赵平津当然认得他,他坐在摄影棚看着这个人有一个星期,他跟吴贞贞对戏,下了戏,脸都是麻木的,一脸的倦怠,助理在端茶倒水地伺候,他只在一边不断吸烟。
那是一首熟悉的粤语老歌。
宽敞的客厅里原本叽叽喳喳的女人忽然安静了,水晶吊灯灼灼闪烁,一方巨大的液晶屏幕,女人们伸长脖子顾着看男明星。
一个略沙哑的男声伴着音乐在唱:“我看见伤心的你……哭态也绝美……只得轻吻你发边……”
那一霎镜头转到台下的观众,观众席一楼的前几排都是看起来熟悉的却又叫不上名字的各种明星脸,摄影机却直接略过,然后镜头锁定在后排一个女孩子的侧脸。
那是一张近乎完美的剪影。
红的胭脂白的粉,浓眉毛俏鼻子,红唇是一抹饱满的樱桃色,明亮之中却有一股凄凉的哀艳……被拍者毫无知觉,她只是微微仰着头看着舞台,灯光略昏暗,一半的光打在她的脸上。
她仰着头,静静地听着歌声,目光却定在虚空中的某一点。
她美丽的脸颊上,有一行清泪正缓缓落下。
凄美得叫人屏息。
摄影师都起码停了近十秒。
客厅一片安静,高积毅扫了一眼电视,忽然问了一句:“这是新出来的女明星?”
方朗佲悄悄起身,走到了老婆旁边,青青依偎着他感动地说:“好喜欢这首歌。”
高积毅也站了起来,走过去兴致勃勃地跟着看电视:“舟子,让人打电话去电视台问问,那美人儿是谁?”
高积毅的媳妇儿在旁叫了一声:“喂,老高!”
高积毅没个正形:“夫人息怒,这不是还有未婚的吗?”
大家都往赵平津看过去,赵平津一动不动地坐在茶几旁边,一张英俊的脸,脸孔发白,结满寒霜。
陆晓江坐在他的对面,不知为什么突然无端觉得紧张,把手压在膝盖上,止住了想要发抖的手臂。
高积毅还在客厅那边叫唤:“哎,舟舟,你快过来看看还有没有镜头,那姑娘真挺美。”
赵平津倏地站了起来,将手里一个茶杯往桌面上狠狠地一扔,正砸到陆晓江跟前。他简直不知道使了多少力,上好的古瓷摔得四分五裂,瓷片碎渣子瞬间溅了一地,陆晓江直觉伸手挡住,手臂顿时一道血迹流了下来。
一屋子人顿时都傻了,没一个人出声。
赵平津一把抓起烟盒,在失控之前说:“我出去抽支烟。”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青青在那边说:“晓江,有没有事?”
陆晓江摇摇头,抽了张纸巾擦了擦那道血迹。
高积毅纳闷地道:“这戏又是唱的哪出啊?”
方朗佲飘飘然地冒了一句:“黄西棠。”
高积毅没反应过来:“什么?”
方朗佲说:“刚刚那姑娘。”
高积毅彻底哑巴了。
陆晓江脸色慢慢地变了。
只有高积毅的老婆一脸好奇:“黄西棠是谁?”
方朗佲看了看手机,有点担心:“他这么出去,行不行?”
十分钟后,赵平津没有回来,打电话过去去,一开始不接,再打就关机了。
高积毅回过神来:“他今天带司机来了吗?”
陆晓江有点慌张,低声说:“我来的时候在车库里见到他了,他自己开车来的。”
高积毅工作了近十年,处理过的舆情危机不计其数,最擅长就是遇事先找人调停:“别慌,朗佲,先给沈敏打电话。”
一顿饭莫名其妙散了,客人起身告辞,高积毅送方朗佲出去的时候,低声跟他说:“我说怪不得我认不出来,钟巧儿走了一年时,忌日里我在墓园见过她,现在想起来,她脸上不太对劲——”
方朗佲说:“谁?”
高积毅白了一眼:“黄西棠。”
方朗佲奇怪地问:“你什么意思?”
高积毅压低了声音说:“她当时戴着墨镜,我起初没太注意,后来想起来她眼角有一道疤,看着跟毁容差不多似的,是不是舟子……”
方朗佲冷冷地打了个寒战。
赵平津开着车从高积毅小区里的车库出来,穿过朝阳公园的正南门,沿着长安街一路狂踩油门,一直开到了五环外,经过昌平区后仍然不停,几乎要到了温榆河畔。
车子呼啸着穿过大半个北京城,高架桥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一直到车流渐渐稀少,远方黑漆漆的天际露出些许山丘的轮廓。
那张带着泪痕的脸,一直在他眼前徘徊。
他知道那个颁奖晚会,那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那个晚会之前的一个小时,他让人将一串钻石项链送到了她的经纪公司,然后沈敏给倪凯伦和她的经纪公司老总各打了一个电话。
她该明白,她欠他的,始终要还。
那样悲的歌,那样哀切的深情,她一直哭。
她有什么好哭。
那年他也在开车,在凌晨时分经过高速返京,她坐在他的身边。
电台里也是在放港台流行歌。
那时他们吵架正吵得天昏地暗,赵平津有个合同临时要去天津签,他气到干脆自己开车去,拎着她上车,两个人继续吵。
那年京津高速还没开通,他走那条老的京津塘高速,路况不好,他精神差,回来的时候,已经几乎要崩溃。
黄西棠毫不留情地戳破了他们感情的最后一丝遮羞布,她坐在他的身边,却仿佛离他遥远得好像一个陌生人,她只板着脸冷冷地说:“我配不上你高贵的家庭,那你就不要和我在一起啊。”
赵平津伸手耙着头发,焦躁地答:“你就不肯为我暂时委屈一下?这是迂回,你先跟我在一起,取得他们同意了,你再出去拍戏!”
西棠那一刻忽然就火了:“他们不喜欢我!你以为我读研读博你妈就会喜欢我了吗?不会!我告诉你赵平津,你妈看不起我,因为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因为我不是谁谁谁的女儿,因为我没有父母的依傍,因为我出身贫寒一无所有!”
赵平津烦躁地答:“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极端武断?”
那一夜她哭得很伤心,也许是已经预感到这段感情已经走投无路。
他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好好好,你去拍戏。”
黄西棠呜咽着说:“那你怎么办?”
赵平津咬着牙说:“我们八年抗战,绝不分手,要不我们直接去领证,你给我生个孩子?”
凌晨的时候,他们在车后拥抱。
黄西棠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将脸埋在他的肩头,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她呜呜地哭:“赵平津,我爱你,我一辈子都不放开你。”
她的声音还是熟悉的,却忽然间换了一张陌生的脸,在千人万人的颁奖典礼,无动于衷地流泪。
赵平津忽然觉得身体发热。
脑海中慢慢清晰浮现的,是她在盛光之下,毫不自觉地流泪的脸,红的胭脂白的粉,浓眉毛俏鼻子,红唇是一抹饱满的樱桃色……就是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接受了那张脸。
她的灵魂逼迫而出,在他的眼前灼灼发亮。
他从来没有办法抗拒她,他想把她摁倒在地板上,想发疯地吻她洁白的脖颈,想狠狠地把她揉进怀里,擦去她脸上可恨的泪水。
他整个手臂都在颤抖,心脏随着血管在剧烈地鼓动,仿佛下一刻就要刺碎胸腔,恍惚之间脸颊划过温热的液体,他爱到两个人的灵魂都在颤抖的时刻,他最后记得的已经不是她的脸,他刻骨地恨着她最后那一刻轻蔑而嘲讽的神色,那样的眼神望着他,好像望着一堆垃圾。
他掀翻了桌子,她摔倒在地板上,地毯洇出一片凄厉的红。
分手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却在每一次吵架后,陷入了更深更绝望的爱。她拍的电影《橘子少年》入围了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剧组要去法国走红地毯,黄西棠在家里摊开箱子收拾行李出国,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他还记得她跪在地上,忽然回头望着他,手里捏着一把牙刷,哀哀地说了一句:“赵平津,我如果要做演员,是不是一辈子都配不上你?”
他为了挽留这段感情,为了想要跟她在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
她要拥有自由和尊严,她要无拘无束地追求梦想,他只好豁出去跟他整个钢铁般军纪的家庭拼了命。他深知他母亲成见已深,便想方设法从他祖父母处入手,他一得空就跟祖母细细地说她待他有多好。赵平津常常跟他奶奶说,他工作忙,有时候加班多,人姑娘每天晚上下了戏都去给他熬粥,连带他身边的明哥儿和小敏他们的消夜都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他还冒昧托人出面请黄西棠的系主任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夸奖了一番这个刚刚在国际电影节上为国争光的优秀学生,然后将她大学四年的成绩册,她的奖学金证书,林永钏导演对她的评价,悄悄地放在老爷子书桌前。
老爷子一个人戴着老花眼镜,在书房看了两天,最后松了口,那天晚餐的桌上,当着儿子儿媳的面儿,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舟儿,周末带她来家里吃个饭吧。”
他记得那一刻的狂喜。
只是那顿饭后来没有吃成,因为隔了两天,就出事了。
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他原来不过是一个被人踩着往上爬的梯子,最后还要被她推倒奚落。
她凭什么一脸无辜,凭什么一副哀哀切切的神情,她凭什么哭。
怎么会有那么可恨的女人,他恨到了极致,只恨不得直接杀了她,却最终什么也不能做。
眼前忽然一片刺目的灯光乱闪,激烈的喇叭声这时才传入耳中,赵平津愣住了一秒,才直觉地一脚死死地踩尽刹车,手上猛打方向盘,下一刻,车子瞬间撞进路边的防护栏,砰的一声钢板巨响,他的眼泪终于痛痛快快地流了下来。
前座的气囊弹了出来,他觉得轻松了,甚至没有一丝痛楚,恍恍惚惚失去了知觉。
西棠走过机场的客运长廊。
夏季的京城,天空蔚蓝高远,西棠记得以前在电影学院,抬头望过去是无垠的蓝空,鸽子的悠长哨声划过,鼓楼外是大片的绿地,而如今从机场巨大的玻璃窗外,只看得到一片灰蒙蒙的天。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再来过北京。
曾经她多么热爱北京,大而空旷的北方城市,她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定居,跟一个深爱的男人,生活一辈子。
后来她离开时,是躺在救护车上,意识不清,生死当头,再没有什么值得挂念。
这五年来,西棠只来过一次北京,哪里都没有去,火车到了北京西站,她下火车直接去了九公山墓园看钟巧儿。
她知道自己此生已经不再适合北京。
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男人在出站口接到了她,他特地确认问了一句:“黄西棠小姐?”
西棠点点头。
他的脸色那一刻甚至有一丝微微的惊诧,但很快调整了过来,他客客气气地道:“您好,我姓龚,是赵先生的助理。”
西棠杀青了上一部戏,她脑袋上的头发开始冒出来,毛茸茸的两三寸,公司造型师给她修了一下。
有点像个清秀可人的小男生。
她神色有点呆呆的:“他怎么了?”
龚祺说:“车子好,没大事,沈先生走不开,特地吩咐我来。”
医院里,赵平津午睡醒来,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影,缩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抱着枕头打瞌睡。
赵平津叫了一声她名字,有气无力的:“喂,你怎么来了?”
西棠也没睡着,闻言站起来:“你醒了?要喝水吗?”
赵平津点点头,西棠将水杯端过去给他。赵平津伸手去接,右手动了动,却忍不住直皱眉,他胸口撞断了两根肋骨,造成气胸和积血,所幸内脏没大事,胸口绑着绷带,他受不了疼,天天要打止疼药。
西棠看见他脸都白了:“要叫护士吗?”
赵平津没好气地答:“你就不会自己拿着给我喝?”
晚饭时候西棠给他喂饭,赵平津这几天干躺着什么也不能做的烦躁心情从见到她忽然就消散了。他看着眼前的人,低眉顺眼地给他挑鱼汤里的刺,乌溜溜的头发新长出来,看得到额头一层软软绒绒的细毛,忍不住嘴角微翘:“哎,这么温良恭俭,下部戏演古装了吧?”
西棠一把将勺子塞进他的嘴巴:“吃你的饭。”
夜里交班医生过来查房,这位也是他的发小,见到西棠在,挤眉弄眼的,嘴上却一本正经:“今天恢复得还可以,舟舟,夜里止痛药减了吧?”
赵平津却认真做了介绍:“这是西棠,这是周子余医生。”
西棠客客气气的:“周医生。”
赵平津说:“子余是上海人,西棠很会做本帮菜,毛蟹和春笋什么的,便宜你小子了,明天白天的班吧,中午过来吃饭。”
西棠会做菜,很小的时候就在厨房给妈妈打下手,到了北京之后,一个鱼米之乡养大的江南女孩儿,为了他开始接触各种面食的制作,赵平津吃得一向讲究,但对黄西棠煮的东西却从不挑食,疙瘩糊了也能面不改色地吃下去。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刚住在一起不久,黄西棠开始学着给他做饭,那一天晚上他下班回来,她从热气腾腾的厨房出来,神气活现地端出了一碗炸酱面。
那一碗面做得非常的漂亮,肉丁被黄酱咕嘟透了,肉皮红亮,面码儿上的香椿芽儿和青豆嘴碧绿一片。
也许是幻觉,他感觉自己吃出了家里老保姆的味道。
她坐在餐桌旁,有点忐忑不安的神情,一直问他好不好吃。
他只是搁下筷子,淡淡地说了一句:“不错。”
哪怕只是这样,黄西棠也乐得欢呼一声,扑过来狠狠地亲他。
他几乎都要忘记了那些时光,她待他,原来也是用过心的。
此刻的黄西棠听到做饭,只在一边对着他干瞪眼。
京城昂贵的私人医院的贵宾病房,跟五星级酒店似,一整个厨房闪闪发亮。
赵平津对她无辜地笑。
那白袍帅气的医生一听就笑了:“真的啊,有口福了,先谢谢了,侬也是上海人?”
西棠上海话说得不地道,也无意跟他攀关系,还是用普通话规规矩矩地答了:“家母是沪上人。”
晚上赵平津打完点滴,早早困了,毕竟还是病人,西棠给他收拾好了换洗衣服,回来房间看见他还醒着,便说:“睡吧。”
赵平津望着她,忽然说:“为什么肯来北京?”
倪凯伦签下的合约里有一条规定,就是她永远不会来北京见他。
西棠也望着他,不痛不痒地答了一句:“沈敏说,加钱。”
赵平津气得骂了一句脏话。
西棠看着他气到发白的脸,扬了扬下巴对他笑了笑,直接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高积毅来探病,一进病房,就看到西棠正给赵平津喂早饭,他一下就乐了:“哟,舟舟,哪来的这小保姆?”
西棠直觉反应回头看了一眼,却又马上转过了头,慢慢放下了碗。
赵平津神色也有点异样,却还是维持住了若无其事的神态:“来了?一块吃点早饭。”
高积毅瞬间也回过了神,迟疑了几秒,思索着称呼,实在难以掂量她在赵平津心中的分量,最终选了个最稳妥的:“黄小姐?”
西棠仿佛没有听见似的,竟没有答他的话,起身擦了擦手,默默地走出去了。
赵平津在病床上叫住她:“喂,你去哪?”
西棠也没理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了。
赵平津一顿早饭吃到一半,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左手不习惯,右手牵动胸前的伤口,疼得直抽气。
高积毅立刻按铃叫护士:“唉,你们这怎么伺候病人的?”
一位年轻的小护士来喂赵平津,一边拾起勺子,一边悄悄地盯着他望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忍不住一直抿嘴偷偷地笑。
高积毅拉了张椅子坐在一旁,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人家护士:“外资医院的护士就是水灵,妹妹,有对象了吗?”
小护士脸颊飞起两朵红晕。
赵平津勉强吃了两口,实在没胃口,叫人走了。
高积毅在一旁啃苹果,一边望着赵平津,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真有那么好?”
赵平津知道他说什么,仰着头躺在病床上,面色平静:“有她在,还觉得人生有点乐趣。”
高积毅点点头,可怜的语气:“你就被她收拾过那么一回,我看你是颓了。”
赵平津眉目之间浮起一层倦意:“过去的事情了,算了。”
高积毅笑笑:“你要真能过去,那就不叫赵平津了,你就揣着这报复心理吧,反正也没事,先玩着吧,最后你会发现也不过就那样。”
赵平津不置可否:“也许是吧。”
高积毅走出去的时候,看到黄西棠站在院子里的小花坛边吸烟。
高积毅站过去,从裤兜里抽出一支烟,含在嘴里说:“借个火?”
西棠将打火机递给他。
高积毅点着了烟,吸了一口,喷出一口烟雾:“你跟舟舟也真挺有缘分,那么多年了,还能凑一块儿。”
西棠依旧没有说话,烟雾中的嘴角,有一抹淡淡嘲讽的笑。
高积毅望了她一眼,她眉眼之间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还在拍戏?”
西棠终于说话:“高先生,我不值得您寒暄。”
她熄了烟转身要走。
高积毅在她的身后慢慢地说:“西棠,你要名要分,将他逼往我们那个圈子游戏规则之外,他的风险太大了。”
西棠无声笑了一下:“我要?高先生你太抬举我了。”
高积毅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眼:“你以为舟舟真那么好,真对你旧情难忘,想要跟你再续前缘?”
西棠站定了,回头对他笑,笑得又纯洁又无暇,她自然知道如何惹恼他们这群不可一世的京城子弟,最好就是千万别拿他当回事儿,一丝一毫也别给他享受那莫名其妙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她笑出了一个拒人千里的弧度:“我怎么想的,关你什么事儿?”
果然高积毅嫌弃地皱了皱眉,抽着烟模模糊糊地道:“外头很多女人想要认识我们这样的人,觉得我们爱玩、大方,手里也有资源。你就看看舟舟吧,京城里数一数二的京城子弟,还长了一张白面皮儿似的俊俏脸,他这些年身边就没断过人,但你们都不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尤其是婚姻,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选择的,他今年估计就要正式进中原董事会办公室了,跟郁家的婚礼也是迟早的事儿,你以为他对你特别一点,就是爱你了?别做梦了,他自小就在这个圈子长大的,如今还混得这么风生水起,什么游戏规则他不懂?你以为他会为了你,毁了跟郁家的关系?”
高积毅冷冷地说:“西棠,我劝你拿点钱,趁早抽身吧。”
西棠身体僵硬,怔怔地站了半晌,突然转过身来,一双眼睛明亮如寒星,直直地盯着他的脸:“高先生,钟巧儿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
高积毅站在花坛边,脸上的笑容如一副狰狞的爪牙:“西棠,你还是那么天真。”
西棠僵硬着身体,一步一步地往住院大楼里挪,走到大厅时候,忽然胃里一阵抽搐,她立刻拔腿就跑,冲进病房区一楼的尽头,撑住了卫生间的洗手盆,喉咙里涌上一阵一阵的腥味,忍不住伏在上面开始呕吐。
钟巧儿走的时候,西棠没有在她身边,甚至连消息都是隔了一个多月后才得知的。钟巧儿在大学时的第一个男朋友廖书儒打电话找到了倪凯伦的公司,然后辗转给西棠带了一封信。西棠打开来,里面掉下一枚戒指,说是钟巧儿遗书里唯一留下的东西,指明要留给她的,说是做个想念。
那是一枚很普通很普通的银饰戒指,西棠也有一个,是大二那一年的圣诞节,她跟钟巧儿一起在校门后的一家小店铺买的。
拿到那枚戒指的时候,西棠躺在自己家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钟巧儿总是爱拉住她的手,柔软暖和的手指曾经拉着她,一起上课、吃饭、逛街,这双手抚摸过她的脸,她的肩,她的身体。
丰满的身体,明艳的发肤,温暖的手指,如今已经全部化作了冰凉的灰烬。
钟巧儿是北京人,但父母早已离异多年,她的身后事是她大哥大嫂和两位朋友操办的,一位是廖书儒,另外一位西棠不认识,但据他描述的样貌,绝对不是高积毅。
西棠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医院里。那段时间西棠住在医院里,钟巧儿戏也不接了,天天去菜市场买菜给她煲汤,晚上就在病房里陪她聊天。西棠一边聊一边哭,她那段时间哭得太多,泪水浸得眼角都发炎溃烂,钟巧儿拿着棉签给她擦消炎药水,擦着擦着开始破口大骂赵平津,直到护士来敲门制止。
亲姐妹也不过如此。
有一天晚上钟巧儿在她耳边说:“高积毅说要带我去欧洲。”
第二天钟巧儿很早就来了,带来了很大一盅排骨汤,还有大袋的水果,然后从那一天后忽然就消失了。
西棠熬过了最难熬的手术恢复期,已经能下床走动,倪凯伦给她请了个护工。
后来西棠听说,高积毅在办离婚,钟巧儿也不知道是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就这样跟着他,她出国之后她们的联系变少了,她给西棠打过几个电话,电话里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她说,高积毅已经离婚了,答应要跟她在一起。
但她最后却只能做一只孤魂野鬼,在深夜京郊别墅区,从楼顶纵身一跃。
西棠拼命地喘息着,冷水扑在脸上,也止不住地干呕,有护士推门进来,问道:“你还好吧?”
西棠摇摇头,把脸洗干净走了出去。
赵平津看着她又回到病房,什么也没说,甚至还将桌面上的碗洗干净了。
她现在很会照顾人,甚至还比以前多了一份细心。赵平津身体免疫力低,伤口愈合得异常困难,夜里胸口的伤常常疼醒,他晚上辗转难安,睡睡醒醒的,每次醒了,西棠都在身边,给他喝温水,跟他说话,想方设法让他好受一点。
赵平津望着她站在他的床边:“你不待见老高,我知道,以后不让你见他就是了。”
西棠一边翻看医嘱,一边确认了药片的剂量,淡淡地应:“没有。”
赵平津那一刻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帮高积毅说了一句话:“钟巧儿的事情,其实也不全是他的责任。”
西棠倏地站了起来,将手上的药瓶子轻轻地放在了柜子上。
赵平津现在已经很熟悉她的神色,看她脸色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眸底的亮光微微发抖,但他就是知道她已经要决裂:“黄西棠——”
她已经走到了外面,拿起沙发上自己的包,直接往外走。
赵平津一手撑着病床坐了起来:“喂!”
偏偏这时外面一个人也没有,黄西棠直接开门走了。
赵平津那一刻只觉心慌无比,想也来不及想,直接伸手拔了点滴,一下床才觉得脚下虚浮,他晃了一下扶着柜子站住了,咬了咬牙追了出去。
他在门外的走廊上拉住了她。
西棠停住了,也不敢动他,只忍耐着说:“放开。”
赵平津这时才觉得胸口的伤处疼,右边手臂连着胸腔里好像重新碎了一遍,喘气带起的气息都在刺痛,他勉强说了一句:“谁准你走了?”
西棠看他一张脸白得跟纸一般,他是拉住她,可她感觉他身体的重量,越来越沉地压在她的手臂上。
“哎,病人怎么起来了?”一个声音在走廊处响起,查房医生来了,后面跟着沈敏。
医生走后,病房内重新恢复了平静。
“老高跟她说了什么?”赵平津躺在床上,大剂量的止痛药打下去,他脸上白得几乎没一点血色,浑身带着一种精疲力竭的虚弱。
沈敏低声道:“听不清。”
“然后呢?”
“她进卫生间,我请一个护士进去看了一下,她在里面呕吐。”
赵平津无力地按了按眉头,眼前有些昏花,模糊中看到客厅外的小人影,趴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
西棠趴在沙发上写菜单,沈敏派人去买。赵平津出了车祸这几天,事情都是他在处理,他不愿家里人知道,找了一间外资医院,他父母这段时间去了江西考察,爷爷奶奶在京郊的别墅休养,他也没有受什么大伤,就想没什么事儿自己对付一下过去就算了。
临近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沈敏陪着李明进来了,身后跟着两个穿西装拎着公文包的男士,有一个是西棠见过的龚祺。
李明跟他一起创的业,如今已是京创第一把手,人倒还是老样子,潇潇洒洒的,一见到她就笑了,冲着她张开了手臂:“棠棠小人儿?”
西棠正腌着鱼呢,摆摆手示意自己手脏,然后客客气气地道:“李先生。”
李明摆起脸:“这么久不见,还见外了?叫明明哥。”
西棠脸色是淡淡的,还是坚持了一句:“李先生。”
身后有下属看着,气氛略有尴尬。
赵平津出声解围,人在病房里喊了一声:“别废话,过来干活。”
房间里临时挪了张桌子,摊开了四台电脑,病床边也能开两个小时的会。
两点的时候周医生来了,赵平津刚刚工作完,精神差,摘了眼镜闭着眼在床上休息。
周医生翻看病例上的数据:“听说早上差点推进去抢救?”
赵平津合着眼倦倦地道:“没有那么夸张。”
周医生收起了病历本:“身体再坏下去,我也不敢再帮你瞒着,赵周两家就你一个,谁不知道你金贵,你要转回军总医院。”
几个男士在客厅里聊着天吃午餐,西棠炖了大骨汤给赵平津,赵平津吃了两口,实在没有胃口,跟她说:“你出去跟他们吃饭吧。”
西棠出去,坐到了沈敏的旁边,仿佛还是跟以前一样,公司里的灯半夜都还亮着,也是他们常常加班,西棠一个小女生跟在赵平津的背后,给他们煮速冻饺子,然后大家挤在一起蘸辣椒酱吃消夜。
赵平津听到外面周子余说:“西棠,吃鱼怎么不用筷子?”
黄西棠轻松的语气:“哎,没事,我比较喜欢勺子。”
她已经将左手锻炼得非常好,能熟练做很多事情,但毕竟不是天生的,有时候她下意识会先用右手,比如端水,拿不稳,然后才突然反应过来。
夜里赵平津醒着,他傍晚时分睡了过去,夜里十点多醒了,西棠说:“要不要喝点雪梨水?”
赵平津摇摇头,然后说:“既然都在医院了,我让沈敏安排你检查一下吧。”
西棠愣了一下,才明白他说什么:“不用了。”
赵平津蹙着眉头:“不要任性。”
西棠说:“凯伦找过很好的医生,已经诊断过了。”
赵平津不屑地道:“倪凯伦找的人算什么,再仔细看看,难道你跟着我出去就一辈子这样用勺子吃饭,也不嫌丢人?”
西棠忽然就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令人惊惧的平静:“我还能这样跟你过一辈子不成?”
早上赵平津心血来潮想吃粥,他今天起得早了些,司机还没上班,西棠出去给他买。
他还指定要宝福坊的鲍鱼粥:“你打车过去,医院门口好打车,完了让师傅等着你,买了马上回来。”
西棠直接给了他个白眼:“金贵,我就在医院食堂买,爱吃不吃。”
她没出去一小会儿,外面的病房门就被推开了,护士过来一般会先敲门,黄西棠还真从食堂给他买了?
赵平津一早起来对着电脑看份重要的文件,头也没抬就说:“这么快?”
“舟儿。”门口传来威严苍老的声音,熟悉的声音唤他名字。
赵平津立刻抬起了头,一位穿着的深蓝色中山装的老者,头发雪白,拄着拐杖,腰杆笔直,目光炯炯。
“爷爷,您怎么来了?”
门外一位穿绸衫的老太太已经抢先走到他身边:“你这孩子,病着不好好休息,怎么还工作?”
赵平津只好合上了电脑:“姥姥,您在北京?”
他父母齐齐站在门外,对着他怒目而视。
保姆司机守在客厅外面,还跟着几个穿白袍的医生护士,偌大的病房里顿时站满了人。
姥姥心疼地看他身上的绷带:“我能不在北京吗?你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瞒着家里,姥姥姥爷可担心了,你妈也真是不像话……”
周女士是独女,蛮横专制的个性也是打小被宠出来的,她就敢直接冲她妈说:“妈,您不是不知道,儿子大了,早就不听我们的了。”
老太太转身板着脸说:“你做母亲的,孩子病床里躺着,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批评你两句怎么了?”
周女士没敢再接话了。
赵老爷子神色威严,声音洪亮,一开口就是不容抗拒的命令:“你这作风纪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开车都能出事,这次出院之后,必须带司机,严禁自己开车。”
赵平津说不上话。
老爷子侧过身,身后的医生走了进来:“这是雷教授,过来看看你的片子。”
他父亲跟着医疗组过去看:“伤得怎么样,治疗了多久了?”
姥姥取过毛巾,替他擦了擦手,心疼地摸他的脸:“瞧瞧,都瘦了。”
一会儿老保姆进来说:“舟哥儿,早餐吃了吗?中午想吃点什么,我回头让家里给你送过来。”
他又望了一眼门外,静悄悄的。
午餐的时候,保姆阿姨照顾他吃饭,父母和姥姥在外面,爷爷返回京郊的屋里,他奶奶早两年查出了老年痴呆症,爷爷不放心老伴儿。
门外空无一人。
黄西棠没有再回来。
十点多的时候,沈敏进来,不动声色地收走了她带来的那个背包,附在他耳边,低声一句:“机票订了,中午十二点的航班。”
他面色平静,点了点头示意知道,一颗心却没办法控制地沉沉落下去。
西棠回到上海,先去倪凯伦那里。倪凯伦在上海的杨浦路有一套宽敞公寓,西棠在上海没房子,倪凯伦直接给她留了一个房间,茶几上堆着一沓剧本,倪凯伦在上面写着一行潦草的英文:读一遍,看看喜欢哪个。
西棠有点兴奋,进公司三年,她第一次有资格挑剧本。
网址:Chapter3 云泥有别乔维安最新章节 http://c.mxgxt.com/news/view/861746
相关内容
当网红遇到明星, 南笙勉强能看, 冯提莫没资格, 网友: 云泥之别最新章节 第一章 大隋盛世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嘿九 ^第12章^ 最新更新:2020
乔安安傅霆深(闪婚后,神秘老公竟是崽崽亲爹精选全文)最新章节列表
《云在风中》慕容之雅 ^第76章^ 最新更新:2015
他乡纵有千金财,难抵故土一撮泥 楚云飞
朗朗和李云迪,同为钢琴家,一夜之间竟成云泥之别
最新章节 副官告白
一朵被践踏至泥泞的玫瑰,还能重新绽放于高贵的枝头吗? 影视剧配音 楚乔传
音乐风云榜春节特别节目 五大明星解析全球乐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