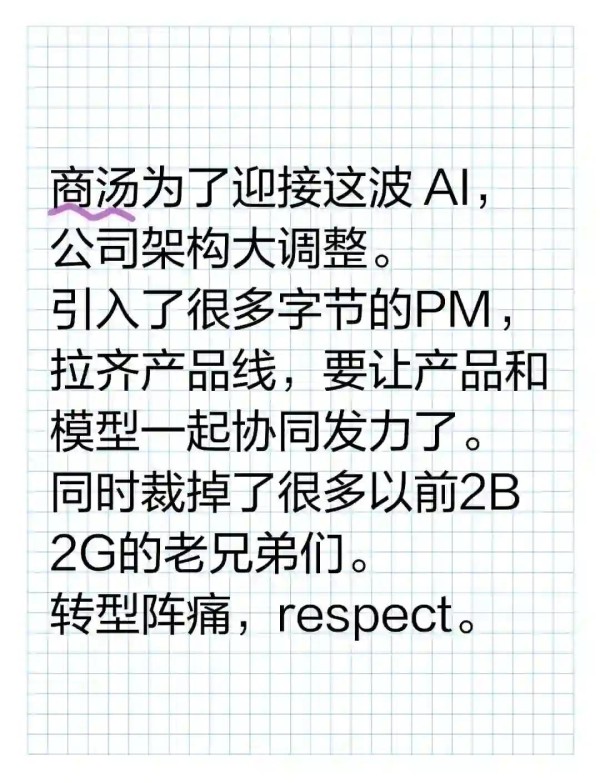社会工作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在我国还处于“准专业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一方面,西方社会工作主张专业关系的建立是以理性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专业关系是达至服务目标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具有工具性而不掺杂情感性,关系双方不需要私人情感的投入,只需要按规则制度建立工作关系,并且这种专业关系可以抽象出来具有普遍适用性与可推广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农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深受熟人社会以及靠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构成的差序格局的影响,这就导致在套用西方专业关系准则去指导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时,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会与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产生冲突,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难以抽离熟人关系而独立存在。这种“中西冲突”致使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陷入了关系多重化及专业关系界限不清晰的困境,对于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乡土中国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熟人关系:
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们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疏程度、感情的深浅程度,而传统的助人关系也建立在熟人关系上,这种关系并不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契约”,而是由助人者与被助者之间的亲疏程度所决定。乡土社会的这一点与现代社会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大多是由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组成,各人不知各人的底细,因此需要契约合同作为双方关系的凭证,若是在乡土社会中也如此,就显得格外见外了。
民间的助人体系是指来自家庭(家族)、亲朋和邻里的帮助,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隶属性,所以家族成员之间的帮助实际上是一种自助行为,而亲朋、邻里之间的帮助则是互助行为,这种自助与互助是由我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决定的;消极低效的求助惯习、相对主动的助人行为、伴随强烈的情感介入。而在家庭之外的支持,必须以责任意识和信任感为基础,由于我国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文化特有的“施报观”的影响,所以“中国传统的求-助关系不是产生于陌生人之间,讲求回报的中国人也不一定希望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付出怎样的回报”。在乡土社会中,凭借同乡之情、同业之缘等,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忙有交往的熟人,虽然彼此之间的关系网络和熟人之间的社会行为模式没有明确的书面标准与准则,但是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中国人(乡土社会中)心中,更是无形地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这些约定俗成的熟人关系习惯规定被打破,硬生生地将建立专业关系的实务技巧和伦理准则嫁接到农村社会工作中,那么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被迅速排挤出这个群体,甚至会成为乡土邻里茶余饭后的笑谈。

专业关系:
制度信任与专业界限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和理论基础,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关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本文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定义概括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社会工作者基于案主利益,为了增进案主福祉而与案主建立的助人关系,这段助人关系是一种职务专业关系而非私人关系,在这段关系中社会工作者和案主是专业关系中的两个角色定位,制度信任和专业界限是建立专业关系的前提和保障。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的首要前提是信任。案主的信任对于社会工作实践工作的开展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只有建立信任后,案主才愿意在社会工作者面前敞露心扉、倾诉心事,这些对于社会工作者正确预估和诊断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制定合理的目标和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信任主要可以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方面,因此发展信任关系也主要有这两个途径。按照西方社会工作的理念,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上,并且是以此为保证的,不需要专业以外的私人情感的投入,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主张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任是一种非个体化的信任,是建立在对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积极预期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所产生的信任关系,与社会工作者个人自身的特质无关,而是因为信任整个社会工作专业,信任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保障。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具有清晰的专业界限是专业关系的重要保障。社会工作者应注重专业关系界限的把握,因为专业关系界限不仅仅是一种专业伦理的坚守,更是因为每一次的越界都可能给案主带来剥削,甚至是伤害,这不能说是为了维护社会工作专业的荣誉,更是出于案主利益考虑,案主利益最大化是达成服务效果的首要保障。
专业关系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实践不仅是专业的实践也是道德的实践,是在专业伦理及职业操守的指引下完成的一系列的专业助人活动。农村地区社会工作受文化因素影响较大,制度信任的建立和专业界限的界定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着更多的新挑战。笔者借助在华中地区的农村社会工作站Y 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来进行探讨。
案例一:在农村社工站Y建立之初,就有村民给单身社会工作者们介绍对象,并希望社会工作者看在熟人关系的面子上和对方见个面,若社会工作者拒绝见面,此人就会产生“你们社会工作者不把我当熟人,不给我面子”的误解,导致社会工作者陷入了从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到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进退两难的境地。
案例二:案主是位七十多岁的独居老奶奶,每次社会工作者去探访她,她都要给社会工作者糖果吃。若社会工作者接受了案主的赠予,就违背了专业伦理,不接受案主的糖果对于案主来说是一种冷冰冰的回应,这也陷入了伦理困境。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我国乡土社会中熟人关系这一本土特质导致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在乡土人情社会“行不通”。笔者认为,既然熟人关系在我国农村社会无处不在,如何确保此种熟人关系不会影响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专业关系的建立,成为本土情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处于这一情境中的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就应当积极探索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发挥熟人关系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积极作用,而绝非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准则。
本土化视阈下专业关系的建立路径
社会工作专业注重强调“人在情境中”,在我国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时这个情境说的就是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时间较短,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本土化视阈下专业关系的建立路径应是渐进性的“专业”,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的认同度不高,还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本土经验的归纳总结,制定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以指导社会工作实践,力求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设转向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建设。
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应该选择从实践过程中的实际体会出发,在综合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在本土情境里尝试建立和应用切实可行、适合国情的专业关系。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信任。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仅有30年,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无法单纯地建立起制度信任。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乡土社会中更亲近于人际信任,但是,建立人际信任,就可能使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私人关系,因此,中国本土情境下的社会工作专业信任模式应是传统社会的人际信任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信任相结合。为了与案主建立工作关系,在本土文化情境下,作为陌生人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与案主建立足够的人际信任,在此信任基础上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特长以增进案主的信任,首先需要向案主澄清角色定位,让村民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有透彻的理解。社会工作者是专业性的,有自己的专业守则,在其角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案主终究会明白社会工作的专业特长同样值得信任。第二,灵活处理本土导向的专业关系界限。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准则,能够使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专业关系时做到“有章可循”,从而保证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棘手、复杂的专业关系时,能够保持一颗客观、清晰的心。专业伦理规定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专业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必须要有界限,但是这种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应有不同的界定,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转换、中和、调整,形成一整套适合我国农村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实践基础上将本土的社会工作经验进行归纳提炼,将本土经验中专业关系界限的把握写入专业关系界限准则,赋予社会工作者更多的灵活处理权。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编辑:谢霄
长
按
解
锁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