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和他的“缓和”时代
1974年9月,为捍卫他所拥护的强调美苏平等共存的“缓和”思想和“缓和”战略,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苦口婆心地全面阐释了“缓和”战略背后的哲学机理: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限制自己的野望和目标,这是因为决策失败的风险超过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他内心也恨不得一蹴而就,但也不得不安于缓进和徐图之道,这就意味着要跟世界的现实妥协、跟美国自己妥协。基辛格坚信,政治家必须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亟需填补本国人民和他的设想之间、本国传统与其未来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一味将政策建筑于人民的经验之上,那政策必将失败。基辛格进而强调,美国在本质上不适应现实主义外交而倾向沉湎于理想主义的道德外交,因而“缓和”理念在美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面临挑战;“缓和”是同苏联这一洲级强国进行马拉松式漫长竞赛的一种长效战略智慧与新型战略文化,其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证明,危机和对抗是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大国关系的日常处理办法。”

当地时间1982年4月27日,英国伦敦,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作为“一个核桃的两个瓤瓣”,在尼克松总统配合下,基辛格本人政治成就以对苏缓和(Detente to Soviet Union)、向中国开放(Open Door to China),以及构筑全球五大力量中心战略稳定体系而日臻高峰同时,他所构筑的对苏“缓和”大厦却逐渐遭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攻讦,以至于新保守主义战略家、里根政府时期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沃尔福威茨指责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生活所在的这个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美国著名外交史家罗伯特·舒尔茨辛格则指出,评估基辛格所做贡献的较好标准,或许应是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思考外交事务的方式、确立重点的方式以及全面看待问题的能力。
由此,对于基辛格成败、功过之评价,在美国极为混乱且伴随政治极化效应而呈现两极化,但从强调不同文明、异质大国共生共存的基辛格所毕生主张的“缓和”思维而言,他确实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宏大实践与谆谆教诲,不仅规训着冷战、成功促进冷战的自我控制自我维稳,更是在未来中长期帮助指引着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大国战略稳定与事关重大的两国永续和平企望。
基辛格现实主义的独特早年经历
的确,基辛格是美国文明的外来者和旁观者。历史学家巴里·葛温在其知识分子史力作《悲剧的必然性:基辛格和他的世界》中,将基辛格与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一起置于逃离大屠杀并被魏玛民主失败所困扰的德国犹太人思想家谱系,以解释基辛格的对外战略偏好。虽然这种归类受到批评,但也不无合理之处。正因为基辛格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外来者,他一方面对大众民主存在疑虑,认为民主的民粹化会引发外交战略失衡,导致国家难以产生真正可靠、长效的外交战略,极右翼势力会利用“苏联威胁”“中国威胁”等意识形态宣教话语深度动员选民,破坏美国的民主,导致美国陷入“敌人缺乏恐惧症”与“威胁通胀”,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破坏美国协调目标与能力的大战略技能;另一方面基辛格从未被美国立国哲学特质中的清教元素及其一元化世界的意识形态特质所绑架,进而他以现实主义的历史机理生发出迥异于美国政治生态的外交战略哲学。此种借鉴欧洲均衡体系与协调外交理路的大战略思维,离不开来自欧陆的基辛格的独特人生体悟与学业经历。
1938年11月跟随父母逃离纳粹德国后,基辛格家族至少有26位亲戚遭到纳粹杀害,幼年时期在德国长期遭受歧视的人生经历导致基辛格初到纽约时十分胆怯,以至于他在马路上散步时如果迎面走来几位美国男青年,他会立刻绕道或去马路另一面从而避开他人。作为二等兵及美军第84步兵师情报人员的基辛格参加二战之经历对他人生影响极大:一方面,基辛格在战争期间遇见年长他15岁、同为德裔美军士兵的高材生弗里茨·克雷默,进而大大激发了青年基辛格对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兴趣,并决心提升自己的学历、改变自身的职业选择;另一方面,基辛格亲自参与解放纳粹德国诸灭绝营的人生体悟对其刺激很大,累累白骨和千里废墟的景象强化了其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哪怕数年之后,基辛格还是无法忘却灭绝营的残酷画面,他1950年时对此写道,“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与西伯利亚劳工营生活过的那一代人是无法做到像他们父辈那样,言谈之中带着同样乐观的语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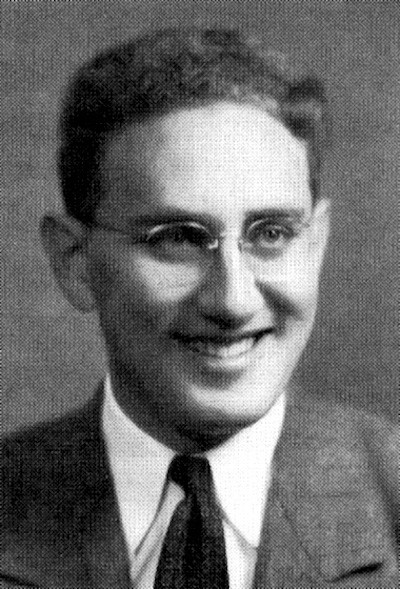
1950年,基辛格在哈佛时期的照片。
二战后,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继续求学经历和学科训练受到当时已闻名遐迩的汉斯·摩根索以及稍早出名的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等学者的现实主义、悲观主义历史哲学之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基辛格认定,生命充满一种内在的命运,但却永远无法定义,历史的伟大进程只能依靠直觉感知,却无法用因果关系去归类。受此影响,基辛格的博士学位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凸显其保守主义思想以及深具悲剧张力的历史哲学内核。
此种强调构筑均势、追求协调外交、现实利益强于道德关怀的学术思路引导基辛格坚信,大国的对外战略决策远非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简单命题,而是在“糟糕”与“不那么糟糕”之间进行权衡的必要妥协。经过数年努力,基辛格于1954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并逐步获得终身教职、获评教授,同期成为共和党大佬、党内温和派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重要智囊。基辛格进而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而得以放手办刊、科研,并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初强化了其“有限核战争”思想以及构筑大国战略稳定结构的相关筹谋。
“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对方活”:基辛格的“缓和”思想
早在1954年,基辛格便深刻观察到苏联对外战略中的“防守本质”,他强调“革命国家的动机也许只是防御性的,它遭到威胁的惶恐之情也许是发自肺腑的。”他继而批评,“过去美国外交政策行为被一些乌托邦思想所激发,认为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世界的根本和谐将会出现”,但这种前景几乎不会呈现。应当说,这一认知颇为精准,但凸显了基辛格的苏联观同当时美国决策层流行的苏联观之大不同。
尤为重要的是,基辛格早在50年代末便强调,美国不应寻求将美式制度强加于新兴国家,应接受并认同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不同于当时正在闪耀的小阿瑟·施莱辛格等自由派学者,基辛格认定,改革苏联的政治社会结构,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接受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接受世界不是美国想要的样子。就此,深受比较悲观的苏联观的影响,基辛格曾于1973年私下对美国海军上将埃尔莫·朱姆沃尔特表示,美国的国家生命像很多其他伟大的文明一样,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美国只能在目前实力均衡的条件下同苏联达成情况最好的交易;基辛格知道自己将成为向苏联做出妥协的谈判者而载入史册,但苏联如同斯巴达而美国则就像雅典,美国人只能怨自己,因为美国缺乏同苏联长久对抗的耐力。朱姆沃尔特后来指出,基辛格的言外之意便是,从历史长远角度来看,实力天平已偏向苏联一边。虽然基辛格后来竭力否认谈话内容,但这次讲话相当著名,吐露了他的真实世界观,这也深刻刺激了美国右翼。
有鉴于此,基于对苏联实力的感知及其未来意图的畏惧,基辛格认定,面对苏联自60年代末以来的强力崛起,美苏“缓和”在道义上、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极为必要的。鉴于暂时无法阻挡苏联成为真正超级大国的趋势,通过借鉴19世纪“欧洲协调”框驭“革命法国”的历史经验,美国需要部分地接受苏联同美国的“对等”和“均衡”地位,进而框驭苏联破坏国际秩序的革命冲动。其中,实现“缓和”的机理在于构筑大国间的行为规则与互动机制,核心在于权力均衡的构建及巩固,据此实现美苏之间基本且可持续的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

1972 年,基辛格(左一)和理查德·尼克森总统(中)在讨论。
通过同尼克松总统的有效配合,以及搭建尼克松——基辛格二元小圈子决策模式,作为总统最为信赖的核心助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水门事件”后兼任国务卿,他同期主导尼克松、福特政府搭建了下述美苏“缓和”的战略框架:(1)美苏相互间谋求以核均势、核稳定和核军控为基础的战略克制与战略稳定,包括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武器协定”(ABM)、美苏“海床协定”等;(2)美苏筹措并维系全球范围内基本的双边行动规则,包括《相互关系基本原则》《防止海上事故协定》《防止核战争协定》、升级双边元首直接联系热线装置以及拟定美苏《互不侵犯条约》等;(3)有选择性地构筑美苏相互依赖制度,并加以维持和变革,据此,美苏相互依赖带来相互义务,可进一步促成双边共同利益和战略稳定的实现。
通过推行“缓和”,基辛格显著提高了70年代前期美国对苏联的技术转让、信贷支持和粮食出口力度,进而曾比较有力地规约了苏联的对外战略行为,以此构筑了美苏大国战略稳定。需要指出的是,与“缓和”战略配合,基辛格同期对华“解冻”外交实为服务于对苏“缓和”战略的附属品,他本人虽也曾希望将美苏“缓和”的诸项机制和规范施用于1977年前的美中关系,当然这一努力并不成功,但上述宏大规划显露出基辛格旨在构筑美、苏、中、日、欧五大力量中心战略稳定结构的夙愿。就此,基辛格推动尼克松政府有效转变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的大战略方向,美国从冷战“十字军战士”和道德洁癖主义者,回溯为以现实国家利益为基准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大国,这有助于美国恢复国力、疗治“越战综合症”创伤,有益于美国根本适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政治生态。
“缓和”衰亡及其评价和遗产
1979年圣诞节,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随即废除年中达成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卡特及后任里根政府旋即大增军费、重建优势,特别是构筑苏联国民经济无法承受的核常武备优势,同时逼促苏联政治转型、废弃美苏平起平坐的战略观、全力打击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活动,对苏“新冷战”自1980年全面爆发,基辛格精心构筑的对苏“缓和”大厦就此崩塌。虽然1987年后美苏逐步达成第三次“缓和”(第一次“缓和”为1959年前后以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为代表的短暂美苏关系“缓和”时期),但以苏联全面收缩、美国逼压苏联及俄罗斯为特征的新时期“缓和”,显著不同于基辛格所勾画的美苏第二次“缓和”结构。
即便1977年起基辛格不再实际参与美国外交决策,但受其思想影响的当年助手和弟子在入仕后积极秉承“缓和”思维,修正着痴迷于意识形态进攻的美国右翼单边主义外交。其中,任福特政府晚期以及老布什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坚信,“缓和”战略促成的美苏大国关系互动的“互惠性”逻辑,是美国在维持军备建设的同时所积极追求的另一对外战略支柱,这一思路也指导着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助手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在1989年对中国的访问策略和持续性的对华“接触”战略总体思路。
但在新保守主义者和一些自由派看来,基于“山巅之城”历史经验的使命感,始终是美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战略传统,美国绝不能仅代表自己的光辉与荣耀,基辛格不顾他国内政而只关注其外交行为进而推动“缓和”的决策,同美国立国哲学抵触,导致美国长期自矜的道德权威大为衰落。他们还认为,基辛格及其助手的“缓和”战略是对凯南勾画的赢得对苏冷战至臻道理的背叛,即“美国需要遵循自己最好的传统,并且证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是值得延续的”。
新保守主义者认定,基辛格所缔造的“缓和”秩序是一种强调强权即真理、超级大国垄断暴力以及相互间恐怖平衡才是解决分歧手段的被动和无良秩序,这一秩序缺乏最为根本的“道德”和“合法”基础,是基辛格无视对苏道德责难而只关注力量问题的妥协办法。鹰派进而强调,美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由主义天命之所在,“缓和”派不能逃避“转型”苏联政治社会模式的道德义务和时代责任,“缓和”的前提应是苏联和东欧“核心政制”之转轨,“缓和”的最终要义应是“终结那些分裂人类的奥理和深渊”。说到底,“缓和”兴衰彰显冷战晚期美国内部有关“相互依赖”与“美国第一”这两种战略理念间的缠斗。而如果我们从内外联结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走向衰亡的同期,正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振、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高潮期,基辛格外交政策逐步被边缘化的同时,正是美国政治极化、文化内战与内部割裂加速恶化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与新保守主义力量相反,共和党温和派及民主党内仍旧保有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支持者和效仿者。福特政府副总统洛克菲勒、卡特政府国务卿塞勒斯·万斯等人士都是对苏“缓和”的坚定支持者,“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也积极认同对苏“缓和”这样一种大国“柔术”,强调基辛格才是真正理解他本意的战略家。凯南和基辛格的惺惺相惜根因于凯南终其一生认定,国际秩序最显著的特质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在全球扩散的美国体制将超出美国的战略能力。美国对外战略的鸽派代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威廉姆·富布莱特也全力赞扬基辛格的对苏“缓和”思想是一种面向未来、对于苏联的估价基于其实际表现,而不是美国战略家一贯从最坏处着眼的有益的大战略,称赞“缓和”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美国肩负的非履行不可的战略义务。
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加以审查可以发现,“缓和”战略是二战后美国“新政联盟”和新政自由主义所亟需的生命线和外交产物,包括共和党内部温和派在内,美国政治光谱中的中左派政治力量往往倾向于开拓并维护美苏关系在内的东西方关系全面“缓和”:如此一来,被压缩的军费开支才可用于公共生产、市民消费和福利提供,国际关系的积极缓和则为美国商品打开了涌入苏联、东欧和中国市场的大门。
由此,基辛格敢于直抒胸臆地大骂美国的右翼力量,强调他们不顾一切地妖魔化苏联、玷污了“缓和”。基辛格亦公开严厉批评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其为了个人权势全力渲染苏联威胁,是他一生中见过的白宫里最腐朽、最危险的人。虽然明知“缓和”日渐遭到美国社会抛弃,但基辛格直至1976年大选前夕仍然苦苦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结构,难道不是国家首要且基本的道义责任吗?即便如此,民众对基辛格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其支持率从1974年的75%至85%,下降到1976年的50%,至1976年11月,基辛格的负面支持率已经远高于当时美国任何其他重要政治家,基辛格已成为当时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中的“负面”符号。即便如此,他仍旧呼吁美国各派亟需珍视“缓和”框架,同苏联维稳大国相互间的权力均势格局,避免陷入对权力优势的痴迷。
基辛格卸任后仍旧长久地遗憾于卡特政府时期对苏“缓和”大厦的动摇,不满于波兰裔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感情用事以及卡特总统的浸礼派牧师气质,认定这些都破坏了他所珍视的“缓和”遗产。对于里根等新保守主义者,基辛格更是嗤之以鼻。他强调,外交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要求有感知未来进而掌握未来的直觉力,美国必须不断学习如何预测未来的陷阱,这更多需要依靠审慎的“常识”,而非建筑于美国天定命运的“天意”,即便国父们和里根等人看到了所谓的“天意”在美国这一边。因此,基辛格非常敬仰现实主义战略家奥托·俾斯麦的名言,“一个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听上帝的脚步声,抓住他的斗篷下摆和他一起走上几步路”。

基辛格
正如基辛格的箴言,公开争取美国的霸权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国际秩序不被视为公正的,任何国际秩序都无法存在;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主导趋势必须是将权力转化为共识,从而使国际秩序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而不是勉强的默认;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道德共识,这种共识可以使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具有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曾经的对苏战略优势论者尼采,亦在晚年呼求全面核裁军,并对美国痴迷于绝对安全、一元化世界进而深陷两场反恐战争深表不安。同样,曾主导深刻卷入越战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以深刻反省美国冷战战略及自身越战作为而发人深省,他认定“美国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
凡此种种,基辛格等“缓和”派战略家认为美国如此一来才能避免陷入保罗·肯尼迪常说的“帝国过度扩张”陷阱、战略透支局面以及泛道德化外交所导致的战略和地缘困境。但事实已十分清晰,赢得冷战、问鼎单极世界的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加速开启同伊斯兰世界、斯拉夫世界和中华文明的对抗,基辛格所担忧的美国“敌人缺乏恐惧症”和“威胁通胀”再度严重,弱化美国国内两极分化和政治极化的系统改革举措则长期不彰。
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由基辛格等战略家构建的“缓和”理念及其实践,一直需要美国决策层及其政治社会生态所珍视、所领悟、所实操:承认国际战略力量结构的多极化前景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多元化特色;就国家安全战略,美国需弱化“绝对安全”执念以及就各领域绝对军事优势的偏执性追求,而应转而奉行大国均势及“相对安全”,实现由过去刚性的、不可持续的美国“统治”“主导”,向美国“领导”“治理”而有序转变。“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美国历史上审慎、明智的决策者所疾呼的“既能使自己活,也能够让对方活”的“缓和”教诲言犹在耳,面对中美实力对比日趋相对平衡与不同文明现代化范式加速演绎的未来世界,美国恐怕终究需要在放弃痴迷“单极时刻”的基础上,去生发另一轮“缓和”思维,去同他者大国共筑另一个全面的“缓和”时代。与此伴随,基辛格的人生体悟与战略智慧值得中美两国战略界和知识界的研究与领悟。
网址:基辛格和他的“缓和”时代 http://c.mxgxt.com/news/view/306687
相关内容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缓和”(détente)战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哪些启示?基辛格谈基辛格:关于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省思
基辛格的风流韵事
基辛格揭秘40年前美国和古巴首次和解是如何失败的
基辛格对话钱颖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95岁的基辛格第六次到访北大 他和学生们聊了啥?
百岁基辛格百次访华,他用半生改变历史进程
全球财经连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逝世
专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基辛格是中美间的一座桥梁”
《新京报》:专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基辛格是中美间的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