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和李安相识的日子(二)
《推手》作为我和李安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真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我正需要学会如何与另一个人达到平衡。就像片名代表的太极招式那样,我需要借他人之力来达到我的目的。这种哲学思想同样体现在导演李安身上,也可以运用在各种自成一派的合作伙伴身上。作为一个被李安锻炼出来的制片人,我认识到了整个生态体现出的共识和异见的平衡:有时你需要推,有时你需要让。
到了拍第二部电影——《喜宴》的时候,我们的预算是150万美元,计划在康涅狄格州拍摄。当时,我们已经有来自台湾的电影制片厂CFPa的70万美元投资,而我们应该设法补齐另一半投资。但由于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其他投资人了,所以这部电影只好用70万美元的成本来完成。为了想办法削减成本,我们的外景经理(location manager)约翰·拉斯(John Rath)说:“特德,为什么要把电影放在康涅狄格州拍呢?如果我们就在纽约拍的话,就可以省下好多交通和住宿的费用了。”我们确实这样做了。说句马后炮的话,这部电影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就像是一封写给纽约的情书。如果我们把它拍成了一部市郊故事片的话,它可能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和价值。由于预算的关系,我们最终是在纽约第十二街的房子里进行拍摄的。这也更容易让人们以为片中的人物是生活在曼哈顿的。
当我们在给电影找销售代理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部片子完全没有卖点。因为它讲的是同性恋,还是个中文片,而且很像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除了它是个讲同性恋的中文片。所有的代理商都说:“这片是卖不出去的。”那时候,我们的资金只剩下2000美元。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用来支付玛丽·简·斯卡尔斯基和安东尼·贝格曼的酬劳;二是用这笔钱买去柏林的机票,自己去柏林电影节上推销这部电影。在玛丽·简和安东尼的祝福下,我们飞到了德国,只带了背包和电脑。我们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这部电影是在媒体看片会上。人们真的都站在了椅子上为它鼓掌。而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在酒店大堂和酒吧里与各种人会面,并最终以相当 于300万美元的价值卖出了这部“卖不出去”的电影。如果《喜宴》 找其他外部销售代理的话,要花上30%的佣金,而我们只收取10%的佣金。所以,结果是:我们完成了第一部卖座片,投资方也赚到了钱。海外销售是我们要涉足的领域。《喜宴》给我的制片费用不到2.5万美元,大约是预算的5%,我和詹姆斯平分了这部分收入。但这部电影的海外销售让我们赚到了30万美元。那时,业界普遍没有想到美国独立电影能在海外有所作为。制片人都没有海外销售公司。那时候,大概只有哈维·维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米拉麦克斯公司会开发、制作和发行独立电影,并且有负责海外销售的部门。

好机器电影制片公司
那时,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艺术以及创造艺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当业界开始认可好机器公司一贯的电影水准之后,我就开始着手把在米拉麦克斯负责国际销售的大卫·林德挖过来。我花了两年时间才成功,但他的到来对公司帮助很大。好机器的国际销售部门是公司成功和实现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甚至在没有直接融资的情况下制作了45部长片,这很大程度上是倚靠海外销售业务实现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卧虎藏龙》。如果说好机器在《喜宴》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我们在李安的另一部电影《冰风暴》上可谓是大步向前。该片改编自里克·穆迪(Rick Moody)的畅销书,是我们做过的成本最高的电影——1500万美元的预算。参与到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制作,并与专业的团队和演员合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给了我结婚的信心。于是,我在完工10天后结婚了。我们集结了一个很棒的团队,预示着我们从从事独立电影走向更为成熟的未来。美术总监马克·弗里德伯格曾指导了好机器的第一部影片——克莱尔·德尼的短片。摄影师弗雷德里克·埃尔姆斯(Frederick Elmes)曾拍摄了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蓝丝绒》(Blue Velvet)。音乐总监亚历克斯·施泰尔马克(Alex Steyermark)参与了许多斯派克·李的电影。剪辑师蒂姆·斯奎尔 斯(Tim Squyres)参与了李安之前的全部电影,后来也参与了大部分李安的电影。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薄弱之处在于我们的服装。拍电影的一大挑战是不能让人显而易见地判断片中的角色和行为。我感觉我们的服装是在呼应时代而不是真正存在于时代中。而时尚这个东西也是最容易引人嘲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越界了,做得过于大胆(这也是唯一一个超支的部门)。尽管我对服装方面颇有微词,但我们有着一群厉害的、有创造力的合作伙伴。他们让我知道,光有拍摄计划、预算、剧本和李安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他列了一个详细的表格,给每个镜头和每个角色写明了可参考的艺术、时尚、政治观点、绘画和书籍)是不够的。真正让影片提升一个档次的是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团队,而且团队里的每个人都那么喜爱李安。制作《冰风暴》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比如要信任他人和信任自己,充分的准备往往大有裨益,以及保持长期的关系及合作的重要性。在拍电影的时候,人们总会担心大家好像在拍不同的电影,因为每个小组的标准和进度不同。在一部故事片的拍摄过程中,一致的调性和水准常常很难保证。但我们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遇 到这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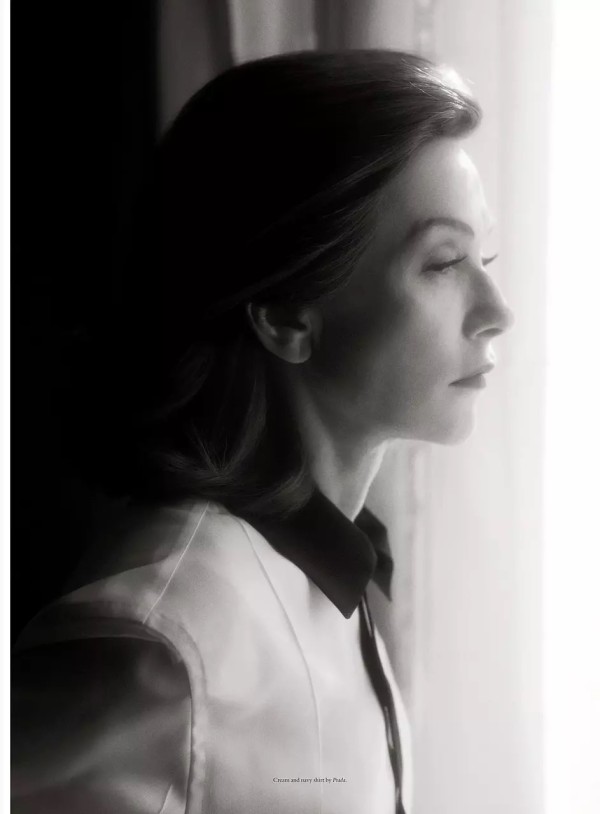
伊莎贝尔·于佩尔
《冰风暴》也是我第一次和明星合作。我们在拍哈尔·哈特利的《业余爱好者》(Amateur)的时候曾和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合作。她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大明星了,但其他美国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福克斯探照灯公司不假思索选了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我们则要去找其他演员。在确定凯文·克兰(Kevin Kline)的时候,我马上发现他和西格妮一样,都在第一时间真真切切地表现出对这个项目的热情。和他们谈合约以及食宿问题的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任何麻烦。以我过去的经验,这些问题往往是像他们这样级别的明星非常关心的。他们简直要把我宠坏了。克兰在片场非常活跃,并且尊重每个人。不论台前还是幕后,他都是如此。这也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很快乐。
有一天,我看到西格尼在剧本上备注了一些东西。我心想,这可不是我们独立电影界的做法。但其实她只是在一场戏上加了备注,就是她的角色在冰风暴来临的当晚和一个年轻男子上床之后回到家的那一幕。她觉得这个在整部电影中都无理对待别人的人,此时需要休息一下。所以她认为有必要加上一幕,就是这个角色像个婴儿一样蜷缩在床上。这可以说是全片最好的镜头之一了。
如果说凯文和西格妮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那琼·艾伦(JoanAllen)则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专业性,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在拍摄最艰苦夜戏的那几天中,有一幕是琼饰演的角色外遇后回家,发现凯文·克兰正在浴室里。这一组镜头我们起码拍了18遍。这是一组推轨镜头,需要在好几处对焦。每一次,琼都准确无误。她就像机器一样精准。之前,我可能对于表演的意义和演员的作用有些嗤之以鼻。但这次经历让我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
李安最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巨大的脑容量(这一点很早之前就能看出来)。他不仅能在脑海中把控正在拍摄的电影,还能在拍摄一部电影的同时准备下一部电影。起初,李安是那种每拍一部电影就不断学习进步的人。所以他常常采用同样的演员并非是偶然。他确实进步很快,而且在拍完三部电影之后(第三部是《饮食男女》),他仍然在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我记得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李安在拍他的第六部电影《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时那么看重动作戏的拍摄。原来,他想要拍一部大成本的动作电影,就像他后来拍的《绿巨人浩克》那样。所以,他一直在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将自己的电影关联起来。
《与魔鬼共骑》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而拍摄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整个过程如同在与魔鬼共骑一般。李安曾经这样跟我说,他对大部分好莱坞的剧本都没什么共鸣。因为那些剧本根本不需要导演,所有的拍摄指导都写在剧本上了,比如哪里需要一个特写镜头,人物当时应该是什么感受等。这些东西应该留给导演去解读。所以,当电影界开始了解李安电影的时候,他便开始要求他的剧本都必须按照他的标准精简。由于李安的编剧詹姆斯·沙姆斯通常也是他的制片人之一,李安提出的要求通常都能得到满足。因为李安电影中所表达的真实情感、复杂情绪以及深刻 细节越来越受到业界认可,业界也开始越来越顺应李安的要求。他不需要别人把这些解释统统写在剧本上。

“好机器”在MOMA举办的作品回顾展上再聚首——大卫·林德、特德·霍普、詹姆斯·沙姆斯。
《与魔鬼共骑》的编剧是我在好机器的制片伙伴詹姆斯·沙姆斯。全片的核心段落是那场著名的劳伦斯惨案。詹姆斯在剧本中这样写道:“劳伦斯遭突袭,惨绝人寰。”这场惨案类似于《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的“亚特兰大陷落”。这句话是剧本中唯一描述场面的语句,只有短短十个字。李安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这留给了他导演的空间。
作为李安的制片人,我和詹姆斯深知劳伦斯突袭这场戏的重要性。我们给这段戏安排了四五天的拍摄时间。我们结合史实编写了 一系列故事梗概,而这些梗概也会根据李安的想法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反复修改和情节展开。我们会为了保证预算砍掉一些段落。让骑兵摧毁一座城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钱。我们的外景经理德克兰·鲍德温(Declan Baldwin)和执行制片人罗伯特·科尔斯布里(Robert Colesberry)找到了一处被洪水冲刷过的小镇。联邦应急管理局想要夷平这个地方。他们已经把居民都安置在了一座山上,建好了学校和基础设施,但这时他们已经没有资金建学校的体育馆了。于是,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这部分资金。相应的,他们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权来决定如何夷平这个地 方。于是,我们在这里给李安搭了一个完美的外景地。
但《与魔鬼共骑》遭遇了票房惨败。1999年,它3200万美元的成本只换回了63.5万美元的票房。有一些事情出了差错,比如在电影制作和发行的时候中途换了制片厂。更严重的是,电影最终的版权方USA电影公司(USA Films)被环球(Universal Studios)收购,而后转卖。因此,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拖油瓶。而且在营销部门的眼里,这部电影简直是那种两边不着调的电影。因为它选用的都是年轻演员,但讲的却是历史故事;它的背景是战争,但中心主题却是情感与良知;它有着大量的枪战戏码,但片中人物却说着戏谑、诗意的话语。歌手珠儿(Jewel)和长相酷似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的斯基特·乌尔里克(Skeet Ulrich)的加盟,使那些本应对它有兴趣的传统艺术电影观众又会对它不屑一顾。所以,片中任何能够吸引特定观众族群的因素之外,都会有另一个完全对立的因素来把这些观众赶走。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并不觉得选珠儿来演是个错误的决定,她在电影里表现得很好。李安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初就希望可以表现出真实的时代感。但让他难受的是,片中所有年轻演员的牙齿都太整齐了,而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会有这么整齐洁白的牙齿。所以,当他看到珠儿的照片和她参差不齐的牙齿时,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事实上,据业界专家所说,一个年轻的牙套妹对于海外买家或者发行商来说毫无市场价值。但一个会演戏又吸引人的流行明星就会有相当大的市场价值。我们让珠儿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来试镜,他们当时都很想加入这部电影。珠儿确实表现得很好。 (没错,莱昂纳多后来还是退出了。李安倒也挺高兴的,因为他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处男,而他认为没有人会觉得莱昂纳多是个处男。也不是说托比·马奎尔[Tobey Maguire]就真的看起来像是个处男,但他毕竟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拍电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为了很好地完成作品,你需要负责一部分工作,而其他人负责另一部分工作。当时我负责制片,詹姆斯负责剧本。剧本改编自丹尼尔·伍德赖尔(Daniel Woodrell)的书《活下去的悲哀》(Woe to Live on)。詹姆斯同时还负责制片厂关系和市场。当时,福克斯的负责人是汤姆·罗思曼(Tom Rothman),他在纽约做独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当他同意我们改编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提了一个条件:电影名里不能出现“悲哀”两个字。于是,我们决定干脆就用“活下去”做电影名,我觉得还挺不错。但就在那一年,张艺谋出了一部《活着》(To Live)。作为华人导演的李安就不能取一个和另一位世界知名中国导演的电影如此相似的片名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另取一个片名。我们找了 一家营销公司来帮忙,但他们取的名字都很可怕。《与魔鬼共骑》对于李安的英语片来说真的是个很烂的名字。它就像是那种机车电影会取的名字,只会吸引那些十八岁左右的小孩。这样一个名字已经将那群艺术电影的传统观众拒于千里之外了。作为制片人,我极力反对这个名字。但我没有成功。制片厂抓着这个名字不放,后来 真的就用了这个名字。
但真正决定电影成败的关键是投资。我们为什么会花3200万美元去拍一部没有观众期待的血腥杀戮,而在那儿心慈手软的美国内战电影呢?
制片厂制作的一大挑战就是在筹到足够的资金来让导演做他想做的东西和做赚钱的电影之间的平衡。如果你是在给制片厂拍电影,那么电影赚钱与否就留给制片厂去决定了。他们负责做生意,而你只要负责精心制作艺术就好了。拍一部尽可能好的电影是制片人的任务,不是制片厂的任务。所以当李安决定要讲一个那样的故事,我便要将它完成。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做。我是否会将这种方法推荐给那些想赚钱的公司呢?不会。但我并不是想做一部赚钱的电影。我是在做一部李安电影。
(本文摘选自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特德·霍普著作《希望为电影:从“纽约无成本制片之王”到产业革新先锋》)
网址:1990年,我和李安相识的日子(二) http://c.mxgxt.com/news/view/721558
相关内容
十二生肖对应的名人明星(1990年是什么属相)1990年,李雪健出演电影《焦...@张二毛Um的动态
1990年属马的明星有哪些
1990年马季为何对李增瑞说:你躲我干嘛?吉他相声也是相声我支持
1990年,李立群和亲哥哥在河南相认,见哥哥穷得叮当响,李立群:哥,我来帮你
1990年,李立群从台湾回到大...@傍晚的暖风的动态
1990年,导演请李雪健主演焦...@治愈系记录的动态
属马和羊属相合不合(1990马和1991羊相配吗)
姓李的四位女明星,我猜你只认识李宇春,若都全认识,我拜你为师
1990年,导演请李雪健主演焦裕...@山中雾啊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