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宁 中华读书报
在庆祝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之际,我们格外怀念季羡林这位清华大学的杰出校友和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我本人和季羡林先生之于这两校的关系恰恰相反:我是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数年的校友和在清华大学任教二十年的教授。季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出于对先生的景仰,在1990年赴欧洲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前,特地拜访了季先生,向他讨教。他给我的一个忠告就是,在欧洲期间一定要去哥廷根一趟。后来,我践行了先生的教诲,在一次会议上有幸结识了哥廷根大学教授霍斯特·图尔克。在他的热情邀请和周密安排下,我实现了访学哥廷根的梦想,并在该校德语语言文学系发表了关于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二十年后,由于我的德国朋友推荐,我被聘请为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前往该校讲学三个月,只可惜此时先生已驾鹤仙去。但他依然活在哥廷根的学子和市民们的心中。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我在哥廷根小城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竟然意外地发现,咖啡馆经理正在翻阅刚出版不久的季先生的《留德十年》德文版。我坦率地告诉他,那只是先生的一部回忆录,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没有外译,如果这些著作译成西方的主要语言,必定会令学界震惊。那么季羡林先生究竟以何种卓越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呢?关于这方面,在十多年前先生去世时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已多有提及。但是对于作为一位文化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季羡林的文化思想和理论建树,则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共识。

《留德十年》,季羡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专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专长是东方学。而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则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并一度有过“苏联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文学批评往往聚焦于西方或俄苏文学,而相比之下,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虽然大部分可称得上批评家的人都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但是也有少数几位专门从事东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型批评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2009年,当被誉为当代“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先生逝世时,不少人竟然只知道他是一位当代文化名人和国学大师,精通多门外语,且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宏论和精致隽永的散文,至于他本来的专业特长是什么,则几乎一无所知。我们首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季先生的学术生平。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随即报名应考并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廷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十年动乱”后的他于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季羡林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是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家中屈指可数的学识渊博同时又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批评大家之一。他同时涉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印度文学翻译及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古代典籍研究以及散文创作八个领域并且成就斐然,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被誉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的学者型批评家。他一生著译甚丰,晚年这些著作和译著汇编成《季羡林全集》,共29卷。其中大部分属于十分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散文作品,还有大量的译著,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批评论著也占了相当的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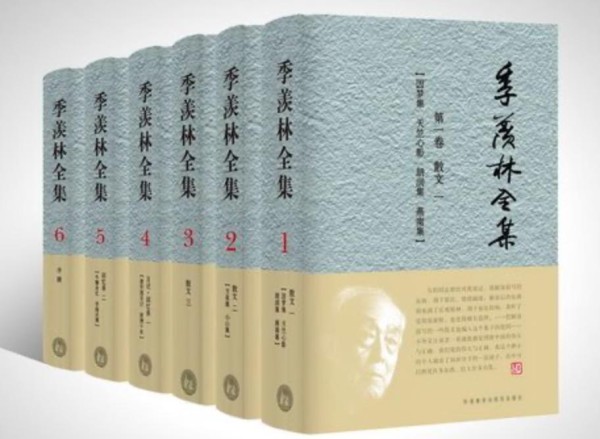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全集》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季羡林的文学批评生涯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自幼学习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而且又有着散文写作的才华,并且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的热点问题,这就使他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写下了一些文学批评文字。在这些批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旁征博引,不仅聚焦于印度文学,同时也涉及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印文学关系,强调中印文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启迪,并提出自己的批评性见解。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他能够利用自己广博的中外文学知识和文化理论思想,率先在中国倡导比较文学和东方文学研究。因此称他为中国当代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并不为过。这也是他的批评文章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外国文学批评家的一个重要方面。
季羡林从事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他始终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在文学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作为一位专事印度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展示这种自古业已存在并沿袭至今的关系。在一篇讨论中印文学关系的文章中,季羡林旁征博引,描述了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印度文学的启迪和影响,他强调指出,中印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并且体现在诸多方面,“到了六朝时代,印度神话和寓言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更加深了,范围更加广了。在这时候,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类新的东西,这就是鬼神志怪的书籍。只要对印度文学稍稍涉猎过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这些鬼神志怪的书籍里面,除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固有的神仙之说以外,还有不少的印度成分。”
当然,他还不止于这种实证性的索隐考证,他同时也不无洞见地指出,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启迪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表现为印度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中国作家作了变通的处理因而被“中国化”了:“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印度人民首先创造,然后宗教家,其中包括佛教和尚,就来借用,借到佛经里面去,随着佛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士感到兴趣,就来加以剽窃,写到自己的书中,有的也用来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劝人信佛;个别的故事甚至流行于中国民间。”这就清晰地梳理了中印文学实际上存在的源远流长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关系,有时这种文学之间的互证和互鉴甚至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涉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
我和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是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而我则是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上进行交流和对话。与一般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季羡林对印度文学中的一些大家和杰作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研究和批评性见解。他虽然主要是一位语言学家,很少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但是他所评论的几位有限的印度古代和现当代作家却是在印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作家。迦梨陀娑这位至今连生卒年月都不确定的伟大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如戏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和抒情诗《云使》等。季羡林尤其对这两部剧作情有独钟,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其从梵文译成中文。他认为《沙恭达罗》体现了古代印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一切美的东西的热爱,并不只是表现在《沙恭达罗》里,在迦梨陀娑的许多著作里都贯穿着这种精神。《鸠摩罗出世》里的波罗伐提表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在《云使》里,尽管那个被罚离开家乡的药叉同爱妻分别,忆念不置,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托云彩给爱妻带讯;但是通篇情调在淡淡的离愁别恨中总有一些乐观的成分,丝毫也不沮丧”。他在对诗人进行评论时,并不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视角出发,贴上诸如“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之类的标签,而是从自己对作家本人的理解和对作品本身的感觉作出自己的评判,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评论这些诗作。
季羡林对现代印度文学也十分喜爱,尤其对现代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表现出由衷的钦佩。泰戈尔是一位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印度文学大家,他的早期诗作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后来生活的现实使他清醒了,他决心为反映现实生活而写作,他的诗歌创作确实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因而他也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季羡林虽然不是主要研究泰戈尔的,但他却广泛阅读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通过将其与欧洲和中国的文学的比较对之作了相当准确的评介。他认为,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也很有成就。按照他的概括,泰戈尔短篇小说有五个特点,首先是他的“单纯的结构”,也即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里,“故事情节的开展仿佛是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浑然天成,一点也看不出匠心经营的痕迹,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均衡匀称,完美无缺”;其二便是他的“形象化的语言”,也即“在早期的小说里,泰戈尔笔下的句子几乎都是平铺直叙的,没有过分雕饰。但是,在简单淳朴的句子堆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几句风格迥然不同的句子,在整段整篇里,显得非常别致”;第三个特点是“比拟的手法”,即使对人物心情的描写也不花多少笔墨,他只须“用形象化的语言”,来一个比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第四个特点是“情景交融的描绘”,具体说来,“在描写风景的时候,泰戈尔不像许多小说家那样长篇大论,他只寥寥几笔,就能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而且“他笔下的风景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与故事的情节,与主人公的心情完全相适应的”;第五个特点就是他的“抒情的笔调”。他认为泰戈尔的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他所受到的国内外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不无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民族传统的影响,这里面包括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民间文学”,正是由于泰戈尔的创作深深地扎根在民族的土壤里,他才最终成为一位蜚声世界的文学大师的。
由于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季羡林中学时代就与他邂逅,但真正理解他却是多年以后。泰戈尔曾来中国访问演讲,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当时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季羡林曾有幸目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风采。虽然当时只有13岁,但是他已经在心目中断定,泰戈尔必定是一位世界名人和大家。1961年正值泰戈尔诞辰百年纪念,年届五十的季羡林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虽然当时并未发表,但多年后,也即1978年,他将其“重新捡出来”并且作了些许补充,又重抄一遍。可见他对这位世界文学大师确实表现了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在这篇题为《泰戈尔与中国》的长篇文章中,季羡林不仅全面地梳理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的评价,而且还借纪念诗人百年诞辰之际向中国读者较为全面但却高度概括地评介了他的文学成就。他认为,虽然泰戈尔著述甚丰,广泛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但他的戏剧创作“是他文学创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因为“他主要还是一个诗人”。
季羡林几乎与国内所有的东方文学研究者都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广博的东西方文学知识和多学科造诣以及对文学理论批评的浓厚兴趣和敏感性。他还就一些方向性的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达到了比较文化批评和研究的高度,对国内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讨论有着导向的作用。作为一位擅长东方文化和文学的批评家,他自然不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他也承认中国文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并对之有着辨证的认识。针对国内一些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季羡林并不简单地反对,反而顺势指出:“我一不发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遭到破坏,对中国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决不能让时代潮流甩在后面。这一点,我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有识之士所共同承认的。”既然西方在近几百年的发展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迎头赶上。季羡林虽然专事东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但他对西方文化所处于的强势和主导地位也不否认,因此他认为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对于国人反观中国文化也不无裨益。
尽管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现在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但局面并非永远如此。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既然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大发感慨,预示“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那么曾在歌德的故乡留学多年的季羡林也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他多次颇有预见性地提出:“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预言一个‘世界文化’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进行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给这种‘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大汇流做准备工作吧。这种研究至少能够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共同保卫世界和平,难道说这不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吗?”可以说,他后来率先倡导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步骤。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后来没有就这种“世界文化”的理论建构再作进一步的深入论证和阐发。
他在比较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后认为,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和局限,这其中不无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西方文化重视分析,而中国文化则重视综合。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沿着分析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越分析越小,因而,在他看来:“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经走得够远了”,该是中国文化登场了。他曾极富远见地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并一度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预言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应验。
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如何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呢?季羡林也有着自己的初步战略构想。上世纪90年代,当国内大多数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依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译介国外文学和理论著作时,季羡林已经清醒地看出了这种译介的一个局限性,也即单向地从西方到东方,具体地说从西方世界到中国,造成的一个结果,也即“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追,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季羡林这位在中国当代学界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家和外国文学批评家也和鲁迅一样在国外受到冷遇,即使在他的母校哥廷根也只有少数人因为有幸读了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的德文译本后才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而他的《糖史》等体现他深厚的学术造诣的许多著作至今却连英译本都没有,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学者的著述了。有鉴于中外文化翻译界的这种巨大的反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理论。因此在季羡林看来,“我们中国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出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国人与有力焉”。他还形象地称这种做法为“送出主义”,与鲁迅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策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过去,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时,鲁迅号召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的文化学术著作,用以促进中国在各方面的现代化。今天,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真正地强起来了,就其综合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何呢?显然,诚如季羡林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因此文化“送出主义”的提出同样展现了他的重要战略眼光,与当年的“拿来主义”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季羡林先生去世后的这些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对于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国文化确实已经走出国门了,但是走出去以后又如何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国内的学界却远未达成共识。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够被别人“找到”并受到邀请的文化学者或艺术家仍然很少,绝大多数人依然在等待自己的作品被国际学界或图书市场“发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因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无须去费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的结局是让世界文化来到中国,或者说让外国人也都用中文来发言和著述。对这种天真的看法季羡林先生早已洞察到。我们也从他的预言中得到启示:不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变得如何强大,中国文化毕竟是一种软实力,也即外国人可以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甚至对于一些针对当代的社会科学文献也会不遗余力地组织人译介,而对于涉及价值观念的人文学科和文化著述,则会想法设法挡住中国文化进入到他们的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近几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孔子学院的抵制甚至将其关闭见出端倪。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季羡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文化送出主义”确实具有一种战略眼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意义将越来越得到证明。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
书业的风向标
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教师学生的课外园地
编辑的案头参考
书店图书馆的采购向导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邮发代号:1-201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60
咨询电话☎️:010-67078085,6707807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原标题:《王宁 | 季羡林之于当今人文学术国际化的意义——纪念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