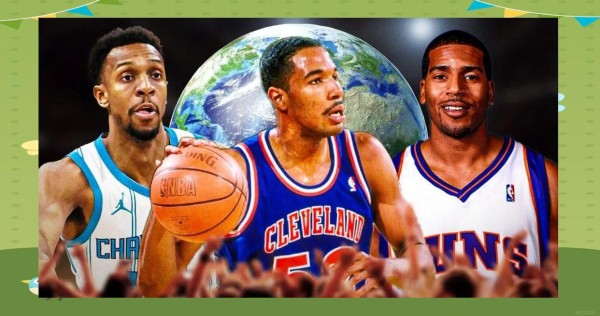陈丹青:我从没忘记自己一直是个老知青(图)
2005.04.15 10:38:12陈丹青之坐而论道——
爱说话、能说话,到处说话
“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
自2000年回国以来,陈丹青以各种形式持续批评“艺术教育之弊”,之外,还就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譬如:
城市建筑——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一城九镇是没有性格的怪物;北京的城建思路是帝都思想作祟,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九州大地的城市建设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行政官与开发商串通,权与利合谋;……
媒体文化——曝光好,曝光有助于人们接近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消除神话——虽然“媒体”、“大众”这两回事大致亦属“神话”,在中国尤其是……
甚至“批评”本身——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诸位批评家要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要自我批评;……
词语也玑珠、话锋也讥诮、立场也独醒、表情也恳切。陈丹青自比“苍蝇嗡嗡叫”,“说话有快感,让我说就好了”——校内校外、台上台下、登报上电视出书。地产公司邀请,去;女性杂志问,答。
为何这样抛头露面?“我在媒体最发达的国家待了那么多年,媒体是空气的一部分。回国发现上媒体仍算一件事,议论、讥嘲、不屑。其实媒体找你,媒体不找你,不算一回事。别把自己看成什么角色,非要怎样,非要不怎样……论角色,我从没忘记自己一直他妈就是个老知青”。
“本质上一直就是个知青”的陈丹青在“事实上”是知青的时候,就非常地“爱辩论”,食堂里、食堂出来的路上,头天晚上不见分晓、第二天接着面红而耳赤……“像个傻逼一样”咬文嚼字、“没有必要地较真”——
“美是有客观标准的”——错!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化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
而如今,写文章,针对一个问题,虽然继续咄咄逼人,继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呱呱呱”;陈丹青自认为已经收敛了许多,还会考虑到“周全”:他会把第一遍意气之作放一放,然后再改再修——“‘所有人’,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所有人’,我怎么能知道‘所有人’?”
“40岁之后吧,也不那么愿意和人辩论了:当发现有了争辩的意思的时候,我就趋向沉默了。”
陈丹青之“起而行”——
不起、不行、不请愿、不结盟
“在许多领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起而行的时代——对我,起而行的前提是,权利对等。”
辞职,按陈丹青说法,是他“惟一能‘起而行’的事”,因为其他事情“早在表格上被规定好了”。
在其一直关注并发言的领域,比如保护胡同,陈丹青不曾属于任何组织、参与任何签名呼吁活动,更不曾拦截推土机。对此,陈丹青有一套“不作为”理论:“我从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对群众举动我会警惕。萨特写道:‘革命就是在大街上叫喊。’有些事,有些时刻,需要群体和行动,但我期待‘个人’,看重个人的品质,自己判断,自己说话,自己负责。鲁迅先生不主张请愿,是大实话。我在乎单独的状态,在乎言论。一切起于言论。如果哪一天我去做什么,前提是权利对等。”
“一个大致正常的社会,如果出现一个阴谋,人欺负人,你关切,站出来声援、介入、制止,那可能是道德的,而且可能奏效。可是一个大规模不公正的社会,在每个环节上不公正,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反应会很困难:介入?不介入?说话?还是沉默?”
悲观至此,时以“愤青”自称的陈丹青甚至否认了“愤怒”本身。
“愤怒还算奢侈的——你愤怒,说明愤怒之后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你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更糟糕的状态是普遍的怨气、沮丧,无话可说,面无表情,但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件令人愤怒,令人发指的事——譬如两课考试。”
当然,聪明剔透如丹青先生,总会峰回路转——在转来绕去的内心世界,结构他的君子处世之道——然后,再自嘲掉。
“当然很多人在行动了,他们很勇敢、很好……我也很佩服做实事、主持社会公益的人——虽然我有我自私的理由:我要守住,我是个画画的,我在抖,但是我平静,不要冲动,冲动是没用的——但仍然会谴责自己:怎么我也变成这样了?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所谓的无奈吧。”
为何这样自嘲?“为什么不自嘲?——自嘲是有快感的。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好,但常有一点遗憾,就是,他们再有点自嘲就好了。”
陈丹青之“个人立场”——不主义、不“正确”、完全的个人
陈丹青的名声大噪,与他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异议”、“不满”是连在一起的。批评——“辛辣的”、“尖锐的”、“痛快的”、类似的形容词,再加上陈经常提及的“鲁迅”名号,其名声实因“辞清华事件”日日看涨。可就在这当儿,陈丹青,皱着眉头,“竟然”矢口否认——
“我其实非常讨厌鲜明的立场,非常害怕一个人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害怕单一思维的,同时又很正直、很老实的人——你可能在很多立场上看到我,但我又走掉了。‘真实’没有立场,是人给出立场,然后真实就变形。”
不左也不右。左吧,新左派的对“文革”对美国的看法“坚决不能同意”;右吧,“站在弱者一边,不与强权合作”这一点又是“坚决地不能妥协的”。
或者是既左又右?陈丹青,至今仍没有语言洁癖的陈丹青教授,一路都留有赤诚的脚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冬天,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看大字报;与“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星星画派”勾肩搭背喝酒听录音机骂人谈艺术;……但是,欣赏并自称“一直站在左翼的、激进的、不安的、冒险的现代艺术一边”的陈丹青,又怀疑——
“我从小右翼,不知为什么。刘索拉喜欢摇滚乐,早期的陈凯歌喜欢实验电影,谭盾喜欢摩登音乐,我的许多同行都喜欢现代艺术,努力进入那个系统,我在大立场上和他们不一样。”
有偏激激进一面,有惰性怀旧一面。认定自己“什么主义者也不是”,陈丹青最怕的其实是“正确”。
他说:“我知道我的画、我自己,都毫无价值,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这表情只有一句话: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
这“集体势利的表情”,陈丹青“从小学起”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天到晚如此,你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你往他前面一站,你还没开口,就知道自己错了。”江西插队、北京美院读书,总有人对陈丹青语重心长——“丹青啊,你的画画得还不错,但这个问题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好……甚至到了美国,一切也仿佛在告诉你,艺术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本能地不去凑前卫艺术的热闹——前卫艺术是什么,不就是政治正确吗?我不愿意正确——当年画西藏组画,就是不想正确啊!”
陈丹青之文艺——美的、历史的、自然的,回到感性
“敏感。为什么不敏感?除了敏感、除了观察,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还有别的吗?”
“一切都取决于我看到的。”在遇到冲突、需要判断的时候,陈丹青让自己凭感受说话——“经历‘文革’,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由保守,现代传统,左右,功利的理想的……这些价值坐标都不如我所看见的真实,真实总是更暧昧,更直接。”
眼前这个上上下下一身黑从皮烟盒里取烟抽的美术教授画家陈丹青的“感受”:“美”是核心,记忆是媒介,天人合一是终极。
“连记忆也是感受。你得仔细感受自己的记忆,记忆从不通知你,它自行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趣味、胡同四合院的故都风范,陈丹青城市建筑批判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就是“葆续历史记忆”。
“殖民者当年为什么在中国盖他们的花园洋房?他在异国,在遥远的东方,都牢牢记住要确认自己,住在自己母国的传统建筑中;张大千流亡阿根廷,还花大钱盖中国林园,为什么?他也是要确认自己,活在自己的,民族的生活景观中。”
历史感是自我,亦是自尊。保持尊严,“现代化”不是借口。“为什么英国、法国这样率先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完全不更动它的历史景观与文化景观?整个欧洲引领世界现代化,可是整个欧洲的样貌与传统景观,在经历一战二战那样的狂轰滥炸后至今完好无损。”
可是现在,就是这个现在,粗俗的、白瓷砖的、玻璃幕墙的“现在”,难道不是历史吗?历史不是无数个叠加的现在吗?
“当然。我们今天看见的古物,当时都是新的。当我凝视一幅7世纪的绘画,这幅画仍然属于‘今天’,就在‘此刻’。历史被持续塑造,有些留下来,有些变形,有些消失。我在乎的并非某一可供指认的实物,而是绵延性——在空间中保留并感知时间的维度。”
时间!在绵延的时间的维度里,陈丹青的“对记忆的本能欲望”的另一魔障,更落后、也更审美。
张爱玲、胡兰成、杜月笙、东湖路……流连过这些老上海跌宕的传奇风雅的属地,丹青先生的怀旧直抵——“人与自然、与四季关系更紧密的”农耕文明。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往炉灶里塞柴草,就着油灯看书,听瓦片上的雨……”曾经8年的知青,敏感细腻如丹青先生,对“超市买电饭锅煲的米饭”和“从插秧收获到舂米全程亲手参与的米饭”之区别,对“不方便的生活的美”有诗意的沉溺,亦有失落的清醒——
“我知道现在的怀念也许很虚伪。当我真的在农村的时候,我每天都想逃离。记忆肯定是被淘洗过的。更准确地说,我怀念的,是那个慢的节奏,是恒长、天长地久。照胡兰成的说法,即‘现世的安稳’。我确确实实记得农村生活的一个下午、一个黄昏多么实在,多么长久。”
那么后工业社会、信息网络全球化,从审美的角度看,就那么不可救药吗?
“话不是这么说法。真实的情形是,你一旦进入现代生活,有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就永远失去了。”陈丹青的忧郁更基于“内心失衡”的警觉。“我们没有选择。只有一种生活。除了都市,好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失去了对比,没有参照。在宋元山水画中的生活形态曾经真的存在过,如今荡然无存,只剩下山水画。”
这样“慢的美的”参照,在哪个意义上重要呢?
“一切回到根本——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社会?敏感的人都会这样追问。如果没有参照,你看不清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陈丹青之正义——美的后面、旧的后面,回到常识
品位与情趣的先锋,直觉与感性的大师,陈丹青先生的聪明,有忧国忧民来压阵脚。
欧洲音乐的胜境、宋元山水画的图景,固然令人神往,但衰败肮脏的乡土、城市街头孤独茫然的农民工兄弟,仍然逃不过丹青先生锃亮的眼睛的“默默的注视”——在他堆满画幅和颜料的桌上,就有一本《农民!农民!——从专家到普通人的访谈》!
采访一开始,丹青先生就“无缘无故地”谈到“三农问题”——“现在的中国农村为什么衰败?没有私啊,没有私产哪会有公心?物质的精神的视觉的心理的,都没有自己的东西,生活本身也就不再是你的。世世代代,这个院子是你的,院子外面的桃树枣树竹林子是你的,你怎会不侍弄不爱惜?国家现在停止农村赋税了,休养生息,都是老办法,都在往回调整。回到常识,多少代价,多么难。”
警惕“美”后面的“匮乏”,亦警惕“旧”后面的“恶”。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好看;“但我不会用那样的方式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其他东西。”——“当年的红卫兵也是这样,因为没长征过,没穿过草鞋,没抗战过,所以要打着红旗要穿草鞋重走长征路——所谓人生模仿艺术——抗日,对经历的人是血与火;对我们,是艺术,是电影和小说。”
虽以画家之正职、教授之公务,对“美”专业研讨之外,踊跃地插嘴“真与善”的地盘,陈丹青对“管闲事的责任感”本身,亦有挑剔。
历史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我开口说话,根本不想到责任感。我们从小被告知‘身负重任’,这类大字眼早已对我不奏效了。我真的对什么负有责任感么?别人会一再告诉我:你的西藏组画很重要;你现在呼吁教育改革,更重要……我会警惕。什么责任、贡献、作用……我不会夸张自己的影响。美国电视常有英雄救人,助人为乐的报道,可是那些当事人说得非常朴素,比中国农民说话朴素多了。人家没有教条,没有被集体教训过。人只要在做人便够了。也许是我在国外见过不少有品质的人,艺术家、大腕,可是他们谦逊平实,从不夸张自己。如果你有责任感,不必表达,或者,以更内在的方式表达——这是一种教养。”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是的,媒体会按照媒体或公众的意图塑造另一个你。现在我得学会和那个‘我’相处。我无法推开他,也不愿承认那就是我。”
陈丹青之虚无——不“抱腿”、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不投靠任何一种价值观,似乎并没影响他的“安全感”。因为,“我从不考虑安全感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没安全感的环境里——十五六岁时,我逃避下乡但又知道必须下乡,我处在危险当中;下了乡,我想被招工回城,但又可能招不上去回不去城,我处在不安之中……
“我是个画画的,但我曾经连画画的都不是。能从村里调到大队,离公社近了5里,我就知足了……我们都是讨生活,一路讨过来的啊。”
陈丹青之青春与祖国——
遥望、眷恋、民族国家焦虑
“我的这一切言行,可能有一个总的背景:我离开得太久了。”
“我记得我第一封信写给阿城,写了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望见高速公路,望见无数小汽车哗哗地开,金色朝阳照亮每一辆车身。……还写第一次在卡内基厅看帕尔曼小提琴演奏的印象……我就很激动地写,抽筋似的。”
这是1982年。在“厕所不臭、花儿不香、到处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的美国,陈丹青抱着“出来看看美术馆,看看原作”的简单想法,开始认识西方绘画的根脉;从19世纪假想中被猛地扔到“后现代”,开始一边学习一边谋生的“自动边缘的生活”。
另一方面,陈丹青遥遥地密切地关注中国主流之动变。途径之一是与国内作家朋友阿城、王安忆等密集地通信……“关于祖国的”只言片语都很容易让陈丹青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我记得到美国第二年,1983年,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是报道山东潍坊县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拥挤着、欢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可那时我是在纽约,天天看见满大街美国人的集体表情,那种自由了好几辈子的集体表情,忽然看见我的同胞!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他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1982年,陈丹青29岁,出国;2000年,陈丹青47岁,回国。这中间,是记忆,是想象。“我的师尊木心先生说,我们都是带根的流浪人。这个根,就是记忆。以前的生活突然中断了,国外找不到连续的生活经验,无法衔接,你就得自己分泌一种东西,活在其中。”
这记忆,是动荡的青春、是苏醒的祖国。
是——从“插秧回来,涮干净指缝里的血,捧读普希金”的知青,到与不三不四的艺术先锋过从甚密的半官方画家——漫长而动荡的青春;是——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中越战争、《今天》创刊、星星画展,是唱起了“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刚刚醒来的祖国。
然后,新世纪的归来。“很快发现‘个人’又被融化了,变成一个期待被策划、被消费的状态,譬如‘双年展’,出版商,音乐包装啊,一切变成兑换、交易……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巴望自己尽快卖出去。”
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 “我向来讨厌文化激进主义,但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天真,热诚,信念……都他妈给大家主动掐灭了,活活吞咽下去了。”
陈丹青失落。昔日的愤青同志今天都早已“学会调整”,日子过得“好好的”。18年后“我们国家的事物”和18年前他刚到美国时“他们国家的事物”原来差不多——“空调、房地产、股票、期货、别墅、轿车、高速公路、跨国公司、总裁、雇员、咖啡馆、健身房、高尔夫球场、会员俱乐部、豪华宾馆、好莱坞大片、超级明星、‘绯闻’、隆胸、变性、‘小姐’、抢银行、资金转移、肥胖、厌食、厌倦、无聊、压抑、紧张、婚外情、私生子、单亲家庭、毒品、艾滋病、心理医生……
“我发现,在亿万同胞行为习惯的无数变奏与翻版中,伟大祖国安然无恙,并继续迸发着比那个疯狂年代更疯狂、更强大、更莫可名状的生命力。”
多年前从报纸上剪下“潍坊风筝节”照片并保存多年,多情如陈丹青,当他终于归来,当然亦逃不过动容的时刻:在南京,夜凉的街角,陈丹青“吱呷”从自行车上迈下一只脚,递给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一块钱,“一块钱三,两个七毛。”“两个。”陈丹青接过茶蛋,抬脚踏车走人——可身后,他听见老太太的吆喝——“还差你三毛呀,哎呦,谢谢了,谢谢了。”
“当然,这不算什么。”中国人的记忆里难道不有比这更悲凉更酸楚更绝望的时刻?陈丹青说出这细节,旋即以另一个细节克制自己的感情:“这不算什么。小时候闹‘文革’,你上街,常常会看到几百个人围着一个人痛打、吐唾沫,拖过几条街。有时候你发现是儿子在打父亲,或者妻子与众人一起打丈夫,那时,瓯打亲属是革命举动,是自我保护,是集体的疯狂……以塞亚·伯林幼年遭遇俄国革命,目睹街头人群瓯打警察,终生以哲学剖析历史。我们也目睹多少悲惨,至少在我,什么都没做,什么也做不了。”
陈丹青,中年文艺份子陈丹青,先天着一代人严酷粗暴的经历、后天着一个人温柔细腻的修养,因为忧患的家国、因为审美的自我——愤世嫉俗、欲罢不能。